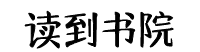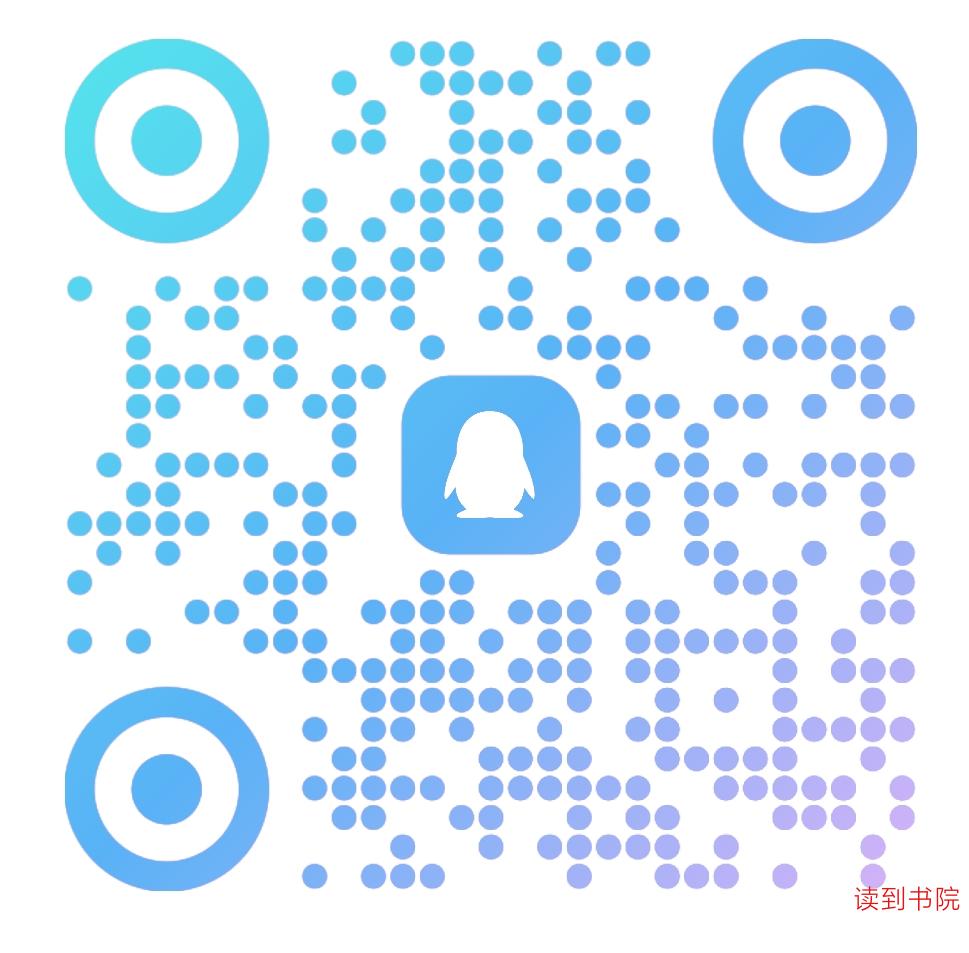1
我有一位年长六岁的兄长,他是父亲的养子徐竟,刚过十二岁生日就去了东瀛。从此千斤重担就落在了自己身上。我深知既肩负家族使命,就需要匹配一颗雄心。
我认为季府必在第六代传人手中复兴,当然这并非指实业之类。我们的财富已经积累得有点过分,它或许会在某个时候散尽。而我真正专注的事业却关乎伟大的永恒,它是这样玄妙而又朴实:服用丹丸,辅以不可言喻的悟想和修持,达到人人都可以看到的活生生的实例。比如说你能够找到一个举止安详、随处透着生机与活泼的一百二十岁的人,会在一座再平常不过的居所里,看到那些忘记了时间的人。是的,时光在这些人身上留不下痕迹,已经不起作用。
父亲在生命终结之前说了一句话:“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他尽管走入了一个终生痛悔的结局,却绝不服输。他最后强调了一个事实:人是不该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人死亡,他自己也未能例外,但正是这种普遍性将一个天大的秘密掩盖了。当这世上的一小部分人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动手去纠正,扎扎实实从头做起时,真正伟大的事业也就开始了。
父亲是季府第五代传人,理应专心致志不屈不挠,可惜他做得不好。他并不怀疑半岛地区流传了几千年的养生术,认为永生是水到渠成的事:只要一个人出生了,也就意味着永生。但要抵达这个理所当然的目标,首先要做到不犯错才行。父亲的死即因为犯错,而且是不可补救的大错。究竟是什么错他没有说,因为时间不够用了。
我今生的任务之一,就是弄清父亲所犯错误的性质与细节。季府遍藏典籍,有一些可称之为秘籍。人人知晓、令人谈虎色变的几千年前的咸阳焚坑事件,烧毁了大量长生不老的秘术,它们都是方士们殷勤西去,献给秦始皇的宝物。其实最深奥的人士都留在了半岛,秘籍也得以保存。季府存下的樟匣中就有这一部分。这些脆弱的简帛和残页在父亲前半生是陪伴的至宝,后来就疏离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父亲止步处重新开始,抄录和装订那些脆弱的典籍,这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我的目光由远及近,寻觅那些不算过于遥远的仙人。半岛是仙人产地,遗踪处处,真要找到一个健在者却要踏破铁鞋。但我绝不能将他们的事迹一概视为传说,那就成了一个愚不可及的人。我造访过不下十余处修炼的洞窟和野屋,还有再平常不过的居家之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户人家:主人常年修持,在一百多岁的某一天,吃过晚饭后与家人一一告别,说一声“我去了”,就缓缓腾空。这个惊人的案例就发生在乾隆末年,就在今天的城郊一带,否认也是枉然。
最为切近的还是自己家族。季府的祖谱就是一部长生记事,上面载有多位百岁寿星和两位“仙化”者。季府简单点说就是一部生命的传奇,如百岁老翁看上去宛若处子,常常令外人闹出辈分颠倒的笑话。传说曾祖父一生都热衷寻仙,一多半时光耗在山野林中,远近岛屿全被勘遍。他曾与一群海上仙人聚在季府喝茶饮酒,客人们来来去去并不乘船驾筏,而是直接从空里走。有一个仙人酒喝多了,半天只升到树梢那么高,淘气的娃娃用弹弓去射,被曾祖父狠掴一掌。
也就在我专心编订族谱的日子里,季府的那个宿敌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2
我至今不能判定自己是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这里指拜邱琪芝为师一事。将一个险恶的仇敌轻轻放过,转而对其钦佩神往,听起来令人震惊。他不把我作为对手,这令我惆怅而又困惑。他完全把我看成一个晚辈,乳臭未干的孩童,几乎不正眼瞧我。对于季府引以为傲的秘传独方,他眼里全是轻蔑,说“啊啊好嘛,我也吃过”。他说那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今天看或无大错,算是聊胜于无吧。”一番话让我怒火中烧,觉得这是当面羞辱。
“比起外施的补益,我更依赖自身。”他慢慢合上了眼睛。
“父亲从来没有放弃,你说的这些,他倒是最用心的。他将补益与吐纳合并,这才是高于你的地方。”我的声音提高了。
他仍旧是平缓懒散的语气:“不可过于用心,也不可过于用力。这话太长了,一时怎么说得完。孩子,这世上没有比我更爱惜你的人了,对你父亲也是一样,可惜他太过用心,你不可学他。”
“你虚伪,而且狂妄!”我怒不可遏。
“他如果在世,也会赞同我这样教导他的孩子。因为他只活了七十四岁,而我一百四十多岁了。”
我一时噎住了。我突然记起了父亲临终的悔疚。我开始细细端量这个不温不火的家伙,发现他如婴儿般细嫩的肌肤下边,正透出一条条青色脉管;额头眉梢,太阳穴那儿,闪着红铜一样的光泽。
我渐渐没了争吵的欲望。因为至少在这个时刻我有些迷惘,发现自己正步于上一代人布下的迷宫。我必须尽快从这个迷宫中逃出,踏上一条清爽宽旷的大道。任何怨怒和激愤、强词夺理的好胜之心,都挡不住逼到眼前的真实。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极为显豁的事实:一是父亲的早逝,二是越活越年轻的百岁之人,是这二者的并置对比。我吸了一口凉气。
他邀我参观丹房,我谢绝了。这样的机会肯定还有,我需要的是尽快回到自己的空间里,好好安定自己。夜晚好长,我失眠了。这在我是极少的情形,因为即便是最亢奋的时候,我只需以意念导引,将激越的心潮平息下去,很快就会迎来一场香甜的安睡。可这一次似乎难以成功,我尽管稍稍用力,却感受不到那种抚平的力量,相反午夜之后蒸腾而起的燥气如野马奔驰。楼下巡夜人脚步清晰,他踏过边楼砖道又折向东,回到更房。我甚至隐约感到了离此一丈之地,还有一个人在甜甜酣睡,她就是仆人朱兰。
从十余年前她就为我伴读,瞌睡袭来,她会用哈气似的声音在耳旁呼唤。我们这样度过了童年,而后自己也就习惯了这样的伴读。有一个无比闷热的午夜,她在一旁挥动绢扇,我却不意间瞥见了薄纱下隆起的双乳,目光不适当地在那儿停留了三五秒钟,让她低头。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娟秀端庄的面庞。在灯光映照下,她的皮肤呈杏红色,且散发出甜杏香气。我紧抿嘴巴盯视纸字,却不知所云。那时我正在新学读书,这是依照了父亲的旨意。新学不同于教会学校,但同样教授算学与西文,除西文不如教会学校之外,其他方面当为最好。校长王保鹤是父亲朋友,这人在养生方面受益于季府,自然对我爱护有加。朱兰每天接送,有时旁听一会儿,夜间陪读时竟能和我一起谈论算学和西文。
这个无眠之夜全是浓浓杏子气味。我披衣长坐,两手抚膝,感受自咽部那儿开始的流灌,它缓缓下行,沉人,驻留一会儿又自行周游,好比一场例行的疆土巡视,最终还回驻地。
3
“我想知道你和季府到底为何分手。”我的声音低沉,但并不急切。在与这个奇怪的对手交往过程中,我总算学到了不匆不忙的本事。我知道这既是深藏不露的心力与谋略,也是一种优雅。
“这句话你早该问了,不过这之前已经答过。我说过太爱季府,因为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安慰我们这些人的了。我想告诉你,季府是半岛地区的这个,”他手指胸口,“心。”邱琪芝重重地吐出一个字,睁开细长眼。
我真的一点不懂,甚至有些慌乱。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府邸藏有长生不老的密钥,它是一些人的指望。季府老爷一举一动都牵着大家的心。我们祖祖辈辈都知道经过无数个朝代,战乱,大养生家死的死隐的隐,有的逃到天外,如今只剩下季府了。”
我心跳加快。因为这无可比拟的、庄严的宣布出自一个敌手。我不动声色地听下去,任何破绽和伪饰都难逃双耳。
“我们不容他人践踏季府声誉,它连接千年根柢,谁也别想拔脱和毁坏。我们最不能答应、最怕看到的是季府的自毁,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站起:“谁在自毁?”
“就是季府老爷,是你父亲。”
“这怎么可能?这真是天大冤枉!他断不会这样……”
“我不想多说了,因为这是说不完的。我只想告诉你,我本来无论怎样也要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可那会儿已经没力气了,我也死了一次。我知道自己吓坏了。我再明白不过的是,我的指望没了。”
邱琪芝好像在泣诉,可是眼里没有一丝泪光。他已经不会哭泣,哀伤也难。我想从中找出什么纰漏,发现很难。隐去的细节太多了,一切只能留待以后。我有倾听的耐心,关于父亲和季府,我可以用自己的一生去倾听。我发现不知不觉间开始信赖这个人,对他后颈上垂下的那根马尾巴不再厌恶。只是对于他所描述的与季府深不可测的情感,还是有些疑虑。
“你父亲离开的那些天我孤单得要死。不错,我还有些朋友,他们散在南南北北,不过全都代替不了季府老爷,半岛上的心不跳了,我们这些人等于全死了。”邱琪芝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翘起,中指和食指有点粗胀。
“前辈,‘我们这些人’指谁呢?”我首次使用了“前辈”这个称谓。
“如果你愿意,还是叫我‘师傅’吧。哦,那些人都散在南南北北,在半岛的,以后自会见识。”
我没有再说什么。说实话,叫“前辈”是一回事,叫“师傅”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季府主人拜了他人为师,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我没有应承也没有回绝。
这一天他引我去了丹房。他的举动令我稍稍吃惊,因为没有哪个人会将外人领进自己的秘修重地。我进入之前当然不会期待看到曾祖父碉楼上的东西,知道这里的“丹”不过是吐纳术的别称。尽管如此,迈人这个幽暗之所还是让我屏住了呼吸。这是一间有着双层木格窗的阔大厅堂,一半铺了毡垫,一半撒了光洁的卵石,由此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卵石部分竖了一个真人大小的木雕,上面刻满了经络穴位。毡垫用以坐卧,一旁是檀木书架,搁满了书籍。帘子垂下后不见一丝光色,但扳动机枢即闪出几个不大的方孔,它们朝向不同的方位。一把紫铜熏壶中冒出若有若无的烟气,厅内是淡淡的檀香味。
令我费解的是木人上标画的穴路,这是任何一位养生者必得熟稔的,为什么还要矗在这儿?我凑近了端量、抚摸,手指感受它坚硬冰凉的质地。每处穴位都凹下一点,好像被霰弹击中。这会儿邱琪芝已赤脚踏上卵石,双目紧闭,绕木雕行走,待步子越来越快时,双手即轮换戳点那些穴位,准确到分毫不差。
我想这是十数年操练的功夫,迷惑的只是其他:对方既不准备技击,又为何如此苦练?为了防身还是其他?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人与他近身缠斗都是相当危险的。我吐出了长长的一口气。
在那朝向不同方位的高高低低的方孔前面,有的是一把木椅,上面带有趴伏的横板;有的只是一根依靠的圆木;还有的什么都没有,不过地上的毡子破损了,可以想见主人常在此站立。
天色已晚,我被挽留一起用餐。他摇了几下手铃,进入隔壁的房间。这是半岛地区才有的席地餐房:地上铺了红篾席子,中间摆放一张精致的小桌。仆人提来一个食盒,从中取出几个碗碟,不过是三样素菜、一碗掺了白米的鱼汤。主食仅为一份稍稍浓稠的米粥。他用餐无语,嚼得很细,吃菜喝粥皆无声音。
饭后端坐原位,过了半个时辰才一起回到丹房。
这里点起了一盏黄黄的圆罩灯烛。一个个方孔全部闭合了。他请我坐到那把带横板的木椅上趴伏,下颌搁上抄起的两臂,然后拉开面前的方孔:一轮满月正从山凹升起,那么大那么圆,清辉四射。我好像从未见过如此皎月,一时凝神。
我好像忘记了身在何方,只看着那轮满月。他拍拍肩膀,我这才醒过神来。他手里端了一个小小的木杯,我接过来饮一口,是玫瑰花茶。搁下杯子,他又让我抵住那根圆木。椎骨贴紧了它,似有一个微凉的活物在后背上蠕动。他打开又一个方孔,它的位置稍稍高过眼睛,我需要微微仰颈。啊,一天繁星闪动,浩瀚无垠的星海天宇。
4
我从头回忆与邱琪芝交往以来的每一个细节,不放过那些对话的任何一句。这是让人费解的一个老人,身上有着完全不同于父亲的气息。父亲当年也许是不得不长期料理实业的缘故,西洋奇巧的应用多多少少改变了他的仪态,比如他戴着花镜一遍遍看酿酒师呈送的图表,会让我想起学堂先生。这种神气我在王保鹤身上也见过。
还有,每当他暗中会见革命党人回来后,那种神态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唇上掺杂了银色的胡须就不像过去那样紧紧贴伏,而是稍稍兴奋地翘起。我知道他并没有安静下来,更没有用意念引导气息。他随手吞下一些丹丸,那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父亲的那些祖传秘籍已经束之高阁了。他后来很少谈论古代方士,也不太愿意接待来访的养生家。有一次一位身穿深色长袍头戴黑帽的道士来到季府,两人只在厅堂交谈了十几分钟。那人是极有名的山林人物,他走后父亲大失所望,说:“我越来越受不了这种黏黏糊糊不清不爽的东西了,稀稀拉拉的胡子,头上那个发髻,都让我受不了。”我至今记得那些场景,那些话,明白这其中包含了太多意味。我发现他与新式学堂的王保鹤先生越发投机,两人畅谈一两个时辰仍旧不倦,有时还招呼我去背诵几句洋文助兴。
王保鹤比父亲小一点,却令父亲无比敬重,见了总要躬身长揖。对方为了在半岛兴办新学几乎耗空万贯家财,开启民智奔波操劳不知疲倦。父亲私下里评议说:“这是几十年来半岛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历史上立有赫赫战功的人都远不及王保鹤,对此我稍有异议,提到了几位疆场英雄。父亲大不以为然:“杀伐而已。”
我知道那些革命党人就是主张杀伐的,可父亲却在暗中与之交往,赠予宝贵的丸丹,显然想让这些人长生。当然父亲也把丸丹交与王保鹤,耐心地为他加减,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我想父亲的晚年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犹疑之中。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专注于养生,也不会是一个好的传人,这可能就是他临终前的愧疚所在。寻求这个答案太难了,远非我的能力所及。我知道这需要邱琪芝的帮助才行。
但我还不想认其为师,这并不妨碍虚心求教。关于“气息”、“目色”、“膳食”、“遥思”这四项,实践他强调的要义还是浅尝辄止,几近朦胧。季府是依仗丹丸的,一剂独方征服了半岛;吐纳术的采用自祖父开始,是否受到了邱琪芝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我和他在一起时就从气息周流的奥秘开始谈起。
邱琪芝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首先以回忆的语调嘲讽了父亲。“我一想起他,就是端坐在那儿双目垂帘的样子。又在引导周身行气了。真气像一小片云彩那样慢慢聚拢,变成细长的一条,像蚯蚓一样往前爬,最后停留在一个地方。这实在是错了……”
“您的意思呢?您与父亲讨论过吗?”
他答非所问:“你的祖父真是一个好人!他执白子,我是说下棋,总是赢我。我执白子他就输了,可他还是执黑。他不在乎输赢……”
5
我承认自己那会儿就像一个幼雏。我以前精研细琢的那些方法经他轻轻拨弄就风化瓦解了。我相信这种毫无戒备与保留的授予,只能来自一种特别深刻的情感与责任。照他的话来讲,那个顽固到不可理喻的季府老爷离世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它的标志当然是年轻传人的出现。他为重新开始的友谊而兴奋不已,愿意付出一切。“我这里,只要你认为有用的即刻拿去,一点都不用犹豫。”他这样说。接下来他以最为清晰扼要的方式,讲授了有关“气息”、“目色”、“膳食”和“遥思”的基本程序及要领,指出这四者是长生的基石。
我一直忍住内心的讶异。在季府的认识中,那些秘传的丹丸才是基石,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辅助。在导师这里则被颠倒过来,也许是照顾到一个季府传人的自尊吧,他并没有让我抛弃那些丹丸。
篇
“餐饮”曾被我误解为吃喝一类,其实是指“目色”。在导师看来世上一切皆有生命与能量,而个人的力量小到不能再小,所以每个人必得谦卑,与万物取得联系时,需用目光去接纳它们,这种联结方式是那样虚幻而又实际:仿佛不经意的一瞥,一切也就开始了。初升的太阳和月亮,还有田野,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我们的生命。
炜
我自此明白了丹房里的方孔作用何在,原来那是使用“目色”的,是个人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的通道。是的,力量来自浩瀚的星空,那是无穷的,至远至深的,给予我们哪怕只有微小的一点,也将是巨大的援助。我在导师身旁仰脸注视,感受来自遥远天幕的一切。他轻语道:“太过用力了。轻淡,微眯即可,这才是采纳。不然就是投放,向外射出的力也就阻止了进入。你需养成平淡的习惯,看所有的事物,一朵花一棵树或一个人,都不能使用咄咄逼人的目光。谦卑,含蓄,那就适当了,那就最好了。”
导师的话突然让我想到了初次相见的那一幕。那时我怒目圆睁,自以为锐不可当,实际在对方眼里是可笑的。我记得那一天他自始至终耷拉着眼皮,像一个孱弱无力的人。我在想,这世上交织着多少目色啊,它们大多太用力了,一遍遍地击打着外部世界,其实已经拒绝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同时也把自己一点点耗尽了。
“没有什么比人的眼睛更贪婪的了,它只要见到想要的东西,就会睁圆睁大,放出强光。比如看到财宝和美女,就是这种眼神。生命就随着这样的目色走散了,投放出很远很远,再也返不回体内了。”
在他的低声细语中,我突然意识到对方绝少使用高声,好像永远都是平缓低沉的,唯恐惊扰了什么。这使我想到声音何尝不是跟随“目色”的,它们的态度和方式都是一致的。谦卑一旦化为了习惯,举手投足也就不同了。
由那个木柱又移到另一边,伏到了那把椅子的横板上。时间早了一点,那就再等一会儿。啊,只一顷刻,月亮从山凹间探出来了,一丝丝向上,所谓冉冉上升。我觉得它在注视自己,美丽慈祥的目光让我垂下眼睫。可我的脸颊已经感受了那种微凉的、洁净无瑕的抚摸。这一刻心中静谧、甜蜜,有某种依恋和慰藉在心底浮动,我想吐露什么又忍住了。
这就是在他的丹房里度过的那个夜晚。
回到季府有一场特别香甜的睡眠。好像这是许久以来唯一没有在睡前施行意念引导的一次,我已完全确信了在自然状态下的那种自由的力量,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清晨起得早,我照了一下镜子,出于谦逊,没用容光焕发四个字形容自己。我到花园里去,朱兰已从小径迎来。她笑吟吟地看我,然后称赞我的气色。她不是恭维。
我们在一丛浓艳的芍药跟前停住了。我以最轻微的目光去迎接朝霞里闪烁的花朵,好像嗅到了平生未知的某种香气:有点像刚掰开的涩果的气味,清清的淡淡的,却十分清晰。这会儿我发现朱兰睁大一双眼睛,蹲下来看着,不由得呼唤了一声。
她转脸看我。她的一双大眼光闪闪的,像花蕊上的露珠在跳荡,高耸的胸前落下一片霞光。我把脸稍稍挪开一点,再次看她时,只轻轻地投去目光。
6
我以为和导师之间似乎不需要找专门的时间去谈“膳食”了,因为有许多共同进餐的机会。我这期间好好领教了一番这个怪异的居所,一边暗暗与季府做着对比。我承认邱琪芝的宅第小多了,也好像过于簇新了,没有时光痕迹的交叠,显得有些单薄。它占据的面积太小,大约只有那个麒麟医院的网球场两倍大。而季府则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是半岛上苍黑沉重的存在,像一头衰老的大象。这头大象卧在那儿痛苦地喘息着,但就是不死。
这儿的主建筑是两层的木头屋,除了几个卧房就是书房,那么多的书积满了空间,也许总量要多于季府。他的存书中铅印的远少于季府,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书房黑漆漆没有光色,拉开帘子则通明耀眼。一条弯廊通着卧室,里面是一个地铺,上面是蜡染花布面料的被褥,一个结实的橡木衣柜,简简单单。到处死一样沉寂,好像四下都没有活人。弯廊从屋角延伸,循着它可以到净身浴屋、厨房、仆人室。原来这里有三两个仆人,他们除了我见过的送餐童子,其余的都很老了。其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头包花巾,长了鹦鹉似的嘴,眯着眼睛,走起路来像在水上漂移,无声无息。他指指他们的背影说:“都是一些小东西。”我开始不解,后来才醒悟过来:他们只是显得年迈,实际年龄不到他的一半。
从主楼通向静坐的草寮、丹房和花园,都由相互连通的长廊串起,让人有一种穿行在迷宫里的感觉。邱琪芝说他一生没有妻室,只有过几个女伴,可惜她们都不能伴他走下去。“您为什么不帮她们?”我有些惋惜。他叹一声:“都是一些不愿修持的人,像火。柴躲开了火,火自己就熄了。”我没有再问。我在想这些不幸的女人,隐隐约约感到他把自己比成“柴”:真的不胖,但还不能说骨瘦如柴。
在经过一间冒着蒸汽的房子时我们进去了。这儿是厨房,很大,差不多有丹房的一半。这是我见到的最复杂的兴炊之所了,大锅小锅垒成一排,还有细细一口深井,几只筒炉。正好是做饭的时候,有三个人在忙碌。摞成高高的小笼屉冒出热气,它们层层揭开,分别装了绿色的菜叶和面饼之类,取出后又推进另一个锅里。还有人从那口深井里提出一个瓦罐,倾倒出黄色的汤汁,浇进一个有盖的陶碗,再把陶碗放人炉上的铜盒。白色蒸汽浓一阵淡一阵,从里面走出一个人,走近了吓得我目瞪口呆。
这个人原来是鹦鹉嘴,与我走了个碰面,让我就近看到了她那双比鹌鹑蛋还要大的灰眼睛里,神色竟是散开的。她几乎并不定睛看人看物。可怕的是她大概嫌热吧,像男人那样光着上身,一对乳房黑乎乎的,像小孩头颅那么大,而且鼓胀着,乳头挑衅地伸直了。我有些蒙。这会儿邱琪芝过来,对她说:“饼好了。”她说:“嗯。”
我们总在丹房隔壁的那间屋子席地用餐。从他盘腿坐下的一刻,“膳食”课就算正式开始了。手提食盒的少年其实是仆人中最年轻的,不过十五六岁,留了女子才有的发髻,双目漆黑如墨。他扎了黑色围裙,下边露出亚麻窄裤裹起的两条细腿。邱琪芝指着他说:“这是我的书童。”
我有些不明白的是,一连多少天在这儿见到的都是少年为吃而忙碌,厨房里也有他的身影。我的目光在少年背影上停留时,邱琪芝说:“人生大事是进食,吃。其余都在其次。”说着把一个瓷扁盒打开,里面是两枚不大的饼。他用竹夹为我取一枚,然后享用自己那一份。我知道一切交谈即要停止。
这只饼软软的,像他这儿的所有食物一样。中间有馅,是松仁和莲子,或者还有栗与藕。它们都绵柔之至,仅能从形貌上分辨,咬进嘴里就混为一体了。口腔中像含了糖饴,沿着上腭滑动,半是咀嚼半是自融地走入食道,快快乐乐奔到腹中去了。然后又是舀绿莹莹的糊糊喝,木勺像拇指那么大。品不出什么.只有青气逼人,细腻滑润。我觉得这是某几种菜蔬磨细了,又掺了莼叶吧,反正滑爽和青气让人做出这样的想象。
最后喝粥。这里几乎每餐都有粥,但餐餐不同。有粟米和南瓜红薯,花生玉米,更有高粱土豆,无不可以为粥,只在这儿一定会与肉糜蛋羹之类混合,烂到不能再烂才行。它们看上去已经是油状的,不似汤汤水水。
我们吃得很慢。如果我自己用餐,那么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足够了。坐上半个时辰后,我问到了那间复杂的厨房,他说这相当于季府的丹房,我说季府哪有丹房啊。“有的,从你曾祖父就开始有了,那个麻烦,盆盆罐罐,火,风箱。有一次坩埚裂了,你曾祖父的左脚趾烫坏了。”我哑口无言。我知道他在说那个碉楼。我可没听说那些轶事啊。我们现在早就不那样了,不过是在一间密室里将各种药物制成丸状。
“膳食的大要就是‘柔和’二字。它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入口之物或养或伤,或损在顷刻,或贻害久远。世人被食物所伤只无察觉,吞饱即好,一天天铸成了大错。其实每样食物先要去掉它的‘刚倔’,厨房主要是做这个的。”
“啊,我明白了,那是尽可能让吃的东西变软。”
“当然。不过生硬凉热和大苦大辛都不宜,它们都是伤人的。所以我们最看重粥食,它是‘柔和’的。‘刚倔’不是蒸煮就能免除的,有的还要放到深井里浸泡。有的食物埋进冬雪,有的挂在树上风干,种种方法你是见过的,都为了一个目的……”
“去掉它们的‘刚倔’。”我接过他的话。
他瞥瞥我,这样三两次,让我不安。后来他的两手一直放在膝上,双目低垂说:
“为师的对你也是一样,先要去掉你的‘刚倔’。”
7
我发现用心揣摩领悟,无论是。气息,,“目色”还是“膳食”之道,入门都是不难的。而要真正深入精髓,还需要漫长的坚持。令人一开始就感到困惑的是“遥思”,它被推迟到最后的阶段,可见别有一种晦涩在。就以前交谈所知,这最后一道关卡确是关于意念的,因为无论如何它还要归于一个“思”字。可是当我就怎样运思请教时,他却背着手走开了,说:“随我读书吧。”
我们安坐毡上,饮茶,取檀木架上的书。四处静到极点。我读到的是一本有关瀛洲水路的古籍,讲水波隐秘、鲛鱼故事、各类船舶。对此领域我并不陌生,因为那个为秦始皇寻访长生不老药的大方士徐福就多次往返这条航路。此书虽然并非写方士东渡,却在描述那一带的海域事迹,引人人胜。
我渐渐忘记了其他,当取起一旁的杯子时茶已凉了。邱琪芝端坐三步外的毡垫上,轻翻书页,唯恐惊动了浮尘。他的茶冒着热气,端杯时眼睛并不离书。半天时光过去了。
第二天仍旧读书。我进人丹房时发现架子上的书已被动过,明白是书童将别处的书又添在上面,已摞得很高了。我不知道这样沉寂的阅读还要多久,只是照旧取过一本。解开函套,精制的木刻本,图文兼备,是关于山野风物、远游实见之类。书中有一些前所未闻的动植物,还有各色怪异的遭遇,所载远超已知的地理疆界,早就是瀛洲之外了。
一天过去了大半。我站起伸展手臂,长长地呼吸。邱琪芝仍旧在翻书,我走近时他全无察觉。这样读过一个长长的段落,他才取过一片松叶夹到书中,抬头问:“你在哪儿?”“我在丹房里。”“刚来吗?”“上午就来了。”“可我听说你昨天在海上,今天又去了野外。”
我一愣,后来才明白他话中的机趣:批评我没有沉浸在书中。我笑笑:“读过了也记住了,不信你可以考我。”“记住与否无妨,只要心思能跟上走就好。”“可是,可是书太多了,这要读多久啊?”
“一辈子。”
“一辈子坐在这儿?那要耽误多少事情。”
“你会忘记坐在哪里。你还会忘记自己。我要问,当你两眼被一个个字牵走,越牵越远,你的心思是不是跟上了?”
“是的,心思走远了。”
“这就是‘遥思’。”
我长时间一声不吭。我在琢磨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困惑,问:“难道只有阅读才能‘遥思’不成?”
“你阅读就一定会有‘遥思’吗?”
我给问住了。我知道有些书是狭促的、逼近的,于是我摇摇头。
“无论做事,读书,只选那些长远的,并且让自己的心思跟上,忘我,这就是‘遥思’了。”
8
原来“遥思”并非刻意思索遥远之物,而是指心思存在的距离,这距离绝不由意念遣送所造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我没有将心中的悟想说出来,只愿由此向前举一反三:他正手扯手将我领向“遥思”之路,以脱离身陷其中的这个时代。不然就会陷入战乱流血,哀号挣扎,是疯狂卷起的涤荡一切的漩涡。我曾自问那个新兴的麒麟医院是不是这场瘟疫的一部分?想回答“是”,可又不能漠视其屡屡挽救生命的诸多奇迹。在痛苦不解中我只好请教了邱琪芝,他听了立刻手指那个医院的方向说:“当然是,灾殃的两面都是一样的,这好比清廷和革命党,二者一定要火拼流血。”
我对这回答似懂非懂。
我日益用心的只是怎样走入玄妙的深处。在舍弃意念的“气息”、若有还无的“目色”、“膳食”与“遥思”的无比坎坷的路径上,奋力攀援却不敢过于倾心。这是微妙不言的尝试和触探,是稍稍孟浪即丧失分寸的冒险。但我知道一切只需坚持,当于某一刻松弛下来的时候,坦途也就来临了。
与此同时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书房中,想同时初尝“化百万册为一页”的升华之道,这是邱琪芝所倡言的。他把百岁人生品咂的全部贡献出来,让我有一种深长的感动。我曾冷静地推算过他的真正年龄,若以祖父在世的事迹来论,那么他现在确有一百四十多岁了。这个结论让我吸了一口凉气。
午夜时分,我在卧榻上不知不觉间又一次感受了气的周流,这让我有些沮丧。我披衣伏到窗前,微眯双目迎接一天繁星,让徐徐移近的清辉、一种凌晨时分才有的沁凉进入肺腑,替代或驱除那该死的意念。可惜这样做有时成功,有时仍无济于事。我不忘按时吞服丹丸,它在体内衍化时好比垂挂的丝绒,滑爽、舒适,自上而下给人以安慰。稍稍令我不安的只是意念本身:如果不是它,我又如何得知丹丸之妙?这真是最不可解的一对矛盾。
不知是否为持久努力和参悟的结果,我发现自己正在发生不难察觉的改变。我的外部体征大有不同,毛发,筋肉,甚至是目光都在日新月异地演化,大致趋向充实粗重或阴郁沉实。我不敢盯视镜中的双目,因为它像紫李子一样滚动,眼皮也像紫李子那样有了一道叠痕,显出甜厚的滋味。双唇红中透着黑绒光泽,让我的手背不忍摩擦。体内总有什么在鼓胀、冲决,双手想把坚强的青檀拂尘柄攥碎。我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强健之力。
因为对饮食的要求大有不同,仆人朱兰颇费了一番功夫。她一遍遍琢磨,设法让所有人口之物变得“柔和”。厨房里的人已经很难满足主人,这让她不得不亲自忙碌。我们时常一块儿研磨粥食,不觉间汗湿额头。她身上的香气与糯米气息混淆一体,令人鼻塞。她的大眼睛总也不能微眯,就像隆起的胸部总也不肯收敛一样。我的下颏生出奇怪的酸痛,不得不去铜盆撩水,以此缓解一下。可是这种酸痛每到与朱兰在一起时就会复发,所以很容易得知病之源头。
午夜时分,某种思念使气流潮涌得到了遏制,因为它正费力地攀越,在一道高高的山岭前知难而退。我惊惧地盯住这夜色中的浑茫,终于辨认出这山岭正是脑海中的沉浮之物,是朱兰高耸的胸部。
夜间无法安眠,白天的阅读也就难以专注。分神不可避免,“遥思”已成奢望。朱兰终于做出了最好的莲粥,它盛在柞木碗中端来,我只吃了几口。糕饼,素汤,只用一点作罢。朱兰试试我的前额,摇头,懊丧地收拾碗碟。她的背影关在门外的一刻,我的手足又一齐灼烫起来,不得不起而疾行,在室内走个不停。
接下的几天我一直宿在了邱琪芝的丹房中,将厚厚的毡垫当成卧床。可是仍旧难以入眠,半夜竟嗅到了毡子上残存的一丝膻气。天亮了,眼睛里布满血丝。我在饮茶时走神,手足又阵阵灼烫。因为我的往复走动,他终于放下了手中的书。我在他面前站定说:“我……没有办法静下来。”
他并不看我,转向一旁。我盯了一会儿沉默的马尾。这束马尾奇怪地抖了一下,他说话了:“我也曾经这样。”
“那该怎么办?”
“没有办法。你自己没有办法,这要有人帮你。”
“谁来帮我?”
“女人,只有她们。”
我在焦愤与羞怒中涌出了大股的泪水。这是积攒了二十余年的苦涩。我大声呼喊:“够了,不要再说了!千万别说了……”
他的手按在我的头顶,又轻轻捋下。在后背那儿,这手停顿了一会儿,最后拍打两下。“可怜的孩子,这是你的一道坎,大胆迈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