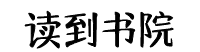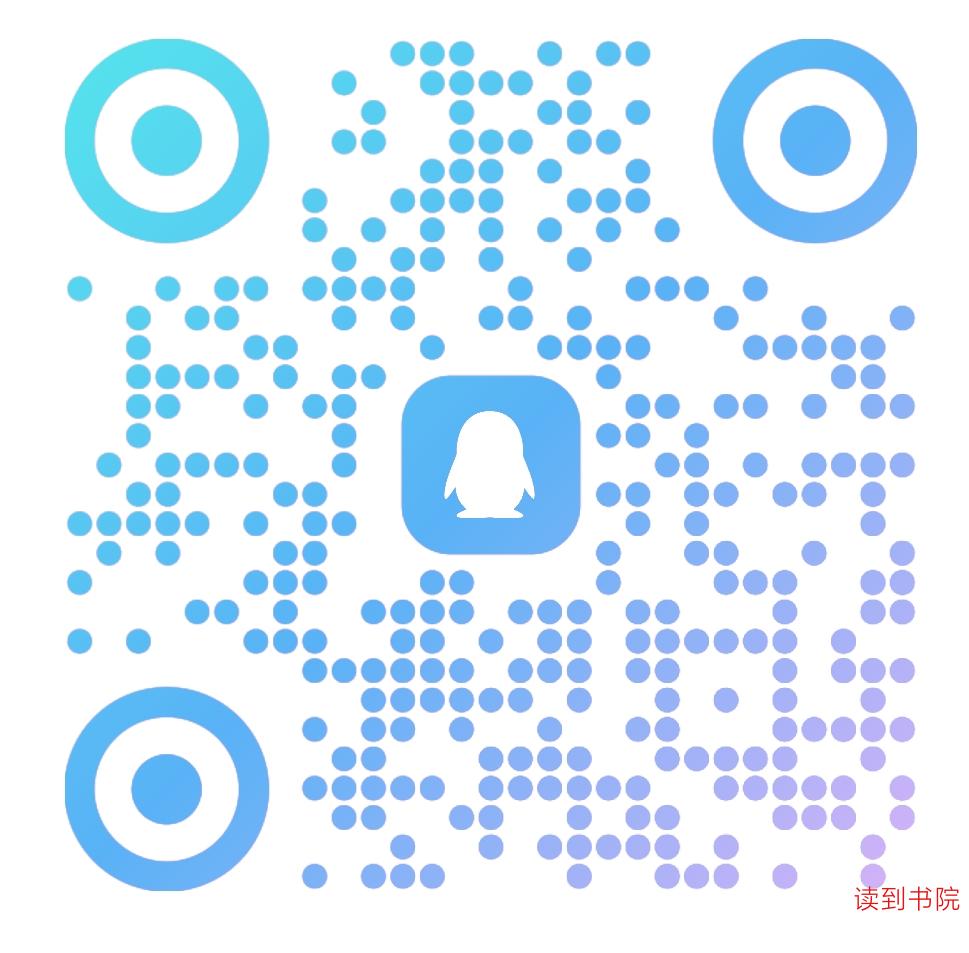1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还记得那天下午,从丹房望出去是一片火烧云,像血一样纵横涂抹了半个天空。邱琪芝还在一旁规劝,哀伤的声音让人难忘,好像在悲悼人生仅有一次的青春。他大概要驱动一支哀兵并令其树立必胜的信心,嗓子颤抖着。他说就一个人的修持来说,大概再也没有比泛滥的欲念更可怕的东西了,它能毁掉一切。而战胜欲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排遣和驱逐,而不是禁锢,“你会咬碎牙关忍着,不过最后剩了一口残牙也还是不成。”
我的目光从那铺天盖地的火烧云挪开,看着他。我想好好聆听。
“要紧的是与她们在一起时不可思来念去,须有个平常心。到了一丝欲念都不存时,你这一道大坎就算迈过去了。记住,人世间没有比欲念更可怕的东西了,你得从头至尾把它去掉。”
我垂着头,两手不自觉间攥紧了。
“去掉它吧。”
他摇了手铃。我退开一步:“不,让我再想一想,也许……”他鼻翼上挂满了鄙夷,这激起了我的怒火。
那个留了发髻的书童进来了。邱琪芝往西北角指一下:“去吧。”书童躬一下身子,在前边引路。
我们在黑漆漆的长廊里拐了几次,然后又往上攀了一层。楼梯不知因为错觉还是果真如此,竟在脚下颤颤地摇晃。在一扇挂了艾草的黑门前边,书童止步,让我自己进去。嚯,好大的一间厅堂,阴暗无光,透着一股怪味。我一直在辨析这似曾相识的气味,但总也想不起来。我拉开帘子想看那片彤云,这才发现整个天空都变成了冷酷的铁青色。余下的天光足以照亮整间屋子,我看清这儿有一张牢固的原色橡木大床,床上铺的仍旧是蜡染花布被褥。床下是和丹房相同的厚毡,上边随意扔了几只枕垫。屋角有一个门,推开门,原来是一间宽敞的净手处,放了大大小小的木桶和水盆之类。
我正发怔,有人进来了。我转身一看差点喊出:这人正是我在厨房里见过的那个鹦鹉嘴,可能刚刚还在灶前忙碌着,这会儿被人差遣过来正有些烦,弯长的上唇绷得更紧,厚厚地包裹着下唇。像我上次见到的一样,她光着上身,两只奇大的黑色乳房沉甸甸地晃动。她极不友善地扫我两眼,回身把门重重地关了,咔咔上闩,然后进了净手间。她在里面哗哗冲洗。
我不知会发生什么奇异的事情。大概这个人一会儿就要离去。我这样想着,哗哗水声停息了,那扇门打开。一股悲酸注满全身,我一动不动僵在了原地。
她走近了,脸上是多少有些不耐烦的、匆忙的神色。她就这样站了片刻,一双散散的大眼睛迎过来,漫不经心地看着我。她身上散发出刺鼻的大茴香味,逼得我后退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跳开,她的粗臂就抬了起来,像一根木梁似的搁上我的肩头。我大口吸气,弥漫四周的全是刺鼻的气味,呛得我泪花闪闪。
鹦鹉嘴转身铺着皱成一团的被褥,让我趁机看清了她门板一样宽、石碾一样圆、泛着古铜色的身躯后影。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臀部下方,那儿有个巨大的凹陷。她转过身,我不敢抬头。这时厅堂里不知何时点起了辉煌的灯火,我在灯火通明中经历着一阵阵颠簸,不发一声。鹦鹉嘴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只是喷气,发出粗重的喘息。最后的时刻她才显出了稍稍满意的神色,散神的大眼眨一眨,厚而弯的上唇翘起来,露出了黑紫色的牙龈。
2
我恨着那个剥夺了自己童贞的人,这个人就是邱琪芝。他经过了精心谋划,终究得逞了。至于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和极度残忍,我也想不明白。大概是深深隐藏的忌恨、捉弄的快意和某些实验的兴趣合在一起,用来加害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我会找到报复的方法,但不知什么时候实施。
一场睡眠花掉了十个钟头,醒来已是半上午时分。朱兰取了丹丸放在床边,端着水。我一双痴呆的目光看着她阳光初照的脸庞和上面一层不易察觉的绒毛,嗓子哽住了。“老爷,早饭都错过了。”她要扶我起床。我握住了软软的、手背上留下浅浅肉窝的手,端上鼻孔深深地嗅着。朱兰脸红了,麻利地抽出手。
我梦见自己被压在大山下边,已经化为齑粉。随着时钟嘀嗒,一个新的我一点点转活了。我下床,第一步差点没有踏稳,朱兰赶紧过来扶住。她说:“老爷,你昨天与什么人打架了吧?”我没有应答。
掺杂了羞愧的愤怒仍旧难以消失,我甚至不无残酷地想象,会有一把尖利的屠宰刀划开某个古铜色的、散发出大茴香味儿的躯体。我永远不会认为那个厅堂里发生的一切仅仅出于良好的用心。我一次次将邱琪芝视为淫荡和阴郁的源头,虽然还有些犹豫不决。
两天两夜过去,深刻的愧疚正转化为另一种急切,而且远超从前。我明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力已经控制了自己,思虑,饮食,更有睡眠,都被它操控。我在镜前注视干燥坚硬的眼球,还有起了白屑的双唇,觉得两脚正急于挪动。“是的,这个魔鬼就是欲望,世上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东西了。”我这时承认那个人的归结或许不错。
仍旧是半下午时分,匆匆赶往那个人的丹房。我的胸前扑满了秋风,可是体内的火焰却在燃烧。
“哦,重症必得重剂,怕的就是半途而废。从根上翦除吧。”他的声音比以前更加哀伤,好像要迎接不得已的死亡。
手铃摇响了。书童步履轻快,进门领人,踏上长廊,再次把我引到那个黑漆漆的门前,然后悄声退去。
有了上一次的经历,我再也不那么匆促,这会儿细细地看了整个空荡的厅堂。厚厚的窗帘。结实的毡垫,那张柞木大床四腿如象足,坚硬如石头。床上的被褥已换成了芍药花图案的,松松软软透着茉莉香味。上一次嗅到的那种怪味已经消散,走到洗手间时却嗅到了一股曼陀罗的气味。季府花园中就有这种植物,它结出的刺果是堵塞鼠洞的良物。
就在伫立走神的一刻,那个人来到了。这一次是扑鼻的香气把我吸引了。转身时,发现一个女子笑吟吟地站在了门口。她有二十多岁,微胖,穿了鲜艳的花衣服,腮上有两个酒窝。我那一刻就在心里叫她“酒窝”了。终于不再是那个鹦鹉嘴,谢天谢地。
她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肩上的针织挎包沉沉的,不时往上耸一下。她那双圆圆的大眼看着我,一直走到跟前,两手搭上我的肩头。这时我才看到她的胸前挂了一个香囊。她满脸喜庆,偶尔伸一下舌头,有些顽皮。我们像一对久已熟悉的友伴一般,既无拘谨也无不适。她的手不离我的双肩。这样坐了一会儿,自然而然地宽衣:木槿花上衣下是绿缎子小袄,然后又是绉纱背心。她打开一旁的挎包让我看,里面有一双绣了一半的彩线鞋垫。原来她正做着刺绣,半截停下就来了。这让我想起那个扔下手头炊事赶来的鹦鹉嘴。她们天生就比我们这些男人忙碌。
她将我的头扳向自己,不断地吻我的头发,双手按着我凸起的脊骨,像刺绣似的一下下移动。她熟练地使用着手语,分毫不差地让我会意。这会儿我才意识到对方从进门那一刻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我迎着她的耳郭呼出一句,没有反应。她一直仰着一张喜庆的笑脸,嫌痒似的缩着脖子,像个娃娃。我的鼻子抽了一下,拥紧她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我好像睡着了,醒来已是灯火灿亮,她在一针针做着刺绣。
我取过那对彩垫看着:上面是一对鸳鸯,已经绣成了大半。我知道这样的礼物通常是女子婚前送给男人的。
3
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这间厅堂,只在喝水吃东西时离开那张坚固的大床,其余时间总在一起。休眠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睡睡醒醒。令我吃惊的是每一次醒来她都在忙里偷闲做着手工,已经绣好了三双彩垫。她见我醒来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小心翼翼地将针线收起,然后给我一个热乎乎的拥抱。我们总是回避亲吻,按邱琪芝所言,这样的时刻最忌纵情。可躲过热吻已经是勉为其难了。酒窝一开始就保持了迷人的微笑,这让我难以遏制。后来才发现,对方的笑靥其实是天生的。
我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沮丧。我试着把平淡的目光投向她,她却仍旧无法收起热忱的脸庞。原来这是一副生就了的表情,不可更改。就此而论,鹦鹉嘴倒是难得的友伴,那何止是冷漠,简直就是一座恐怖的山峦。我这会儿强制自己冷漠、生气,沉着脸去迎接,可惜收效甚微。只一会儿,我的诸般努力不仅全部作废,而且增添了难以控制的游戏感,这反倒使她活泼了许多,干脆不管不顾地将我热吻了三次。我擦擦嘴巴,害怕了。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正在发生,自己喜欢并依赖这个女子了。我觉得她鲜艳如花,温柔可人,是不曾见过的异性伙伴。我们在一起大概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好得超乎想象。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乃至灵魂交给她也没有什么不好,并且不会悔疚。我和她在一起时,已经分不清那热烈的面容和举止有多少是天生的,又有多少是激情的流露。她洁白的牙齿、薄薄的舌头常常显露,因为她看我的时候总是半张着嘴巴。我却要尽力回避这诱惑,转脸去看别的地方。我与之相拥而坐,目光落向她背部的曲线,常常忍不住抚摸起来。但这手触碰到奇异的柔软和温热、微微颤抖的那一刻,立刻要嫌烫似的缩回。
我不敢功亏一篑。是的,在丝绒一样滑润的异性的质地上移动、依偎和行走,太过危险了。我需要一种严苛的心情去抵消幸福和欢爱,以强制而不是迁就的姿态去拒绝自己。我感到那个叫作“欲念”的魔鬼成群地蜂拥过来,它们没有丝毫收敛,倒是愈加放肆和狂热了。它们最后极有可能将我劫持一空。我渐渐感到了胸口下方滋生了一股抽拉的力量,那似乎是向下的、毫不留情的索取,身体中某些至为宝贵的东西正在一点点流失。
我明白要阻止这一切,只有立刻离开这个厅堂。可我同时也知道这里才是遣送魔鬼的场所,在经历了一切必要的烦琐之后,会有胜利的曙光穿过厚厚的布帘射进来。我在一种希冀中抱紧了不可或缺的友伴,浑身战栗着将下巴抵紧了她的肩头。
酒窝所有的表达都依赖手势,那是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仅仅是三个昼夜,我已经弄清了她表述的所有意思。我对她完美无瑕的躯体内包容的丰沛心智感到吃惊。她就像一个适时而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灵,白皙、软胖,时而蜷起四肢,时而松松款款,令人爱不释手。我甚至想在她的足腕拴上红线,因为半岛传说中要留住那些幻化的美物,就得如此。
三个昼夜过去了,我们分开有些艰难。她将散在床上的刺绣品装进包里,又细细清点了一遍,乐呵呵地告别了。她的背影消失那会儿,我心里一片惆怅。
回到丹房,像踏人久违之地。邱琪芝正在翻书,听到响动转过身来。他碰了碰我滑下的一绺头发,上下端量,还攥了攥我的小腿。我感到一阵钻心的饥饿,他却端上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了三杯。“第二天就该让你出来,想了想作罢。这种事不可突兀。跟上次不同,她的火太旺了。”他冷惜地抚着我的后背,拍打着。
我的身体有些摇晃。他说再有一刻就要午餐了,然后竟问起厅堂里的细节,“说实话,我最担心你们俩亲嘴。”我慌慌摇头。“别接火,这是要紧的。那会儿你的手放在哪里?”我躲闪着他的目光。这种回忆是极难的,因为一双手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稍稍满意地垂下眼睛。我想,如果这个人不是有着强烈的窥阴癖,那就一定是太严格了。我还是愿意相信后者,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人,他早已遣送了所有的欲念,这会儿正在指引他人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
这一餐全是粥食。
4
季府里一片死寂,就像我的身体。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喧哗之后,体内各个器官都进入了休眠。我与下人说话时语气淡漠、低沉,在府内活动时脚步变得格外轻缓。管家肖耘雨来禀报时,我仍旧不太人心,最后说一句:“就依你的主意办吧。”他是父亲最信赖的人,年长我二十多岁,府里的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参与。他离去前打量我一会儿,说:“老爷好好将养啊!”
朱兰说近来土匪闹得更凶了,官兵在西郊被杀了几十个,为报复,海防营出动了上千人清剿,打了三天三夜,死伤无数。我出了一头冷汗:屈指算来,那三天三夜正好与酒窝在一起。朱兰时不时过来搀扶,像对待一个易碎品。我偶尔发出一声干咳,她就端来雪梨煎汁,还加上一勺金黄的蜂蜜。她对我一次次离开府邸从不询问,像所有下人那样恪守规矩,却能够洞悉全部的隐秘。母亲去世后,我从她身上寻到了最多的安慰。父亲太忙了,他总是将我交到她的手里。她常常让我骑在她肩上四处走动。终结这个动作的还是父亲,他有一次看到了,厉声说:“下来下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做。
每天总有一段空寂的时间。我的思绪时而徘徊在那间阴暗的、弥漫着曼陀罗气味的厅堂中。鹦鹉嘴沉沉的上唇和散散的眼神让我战栗,须倾尽全力才能从屈辱和痛楚中挣脱。我开始怯怯地思念着酒窝。我害怕了,为这如饥似渴的思念。一股热流伴着被禁绝的意念往上冲决,让我双拳紧握。她美妙的手势,在灿灿灯光下一针针刺绣的姿容,都让我欲罢不能。
深夜时分,云朵遮去星光,漆黑的天宇透出无限的恐怖。我与心中的魔鬼拼搏,力气即将用尽。如果我今夜不能险胜,就将一败涂地。我打开窗子吹了一阵凉风,又狠狠地关上。这响声惊动了一个人的安眠,只一会儿门外就有了轻轻的脚步声。我蜷在沙发上,等待雄鸡啼叫。天迟迟不亮,再也挨不下去。我慌促地披了一件长衣,蹑手蹑脚出门。迈出庭院的第一步,我蓦然回首,一眼发现了倏然亮起的一扇小窗:她正伫立窗前。
我低头继续往前,直奔邱琪芝的宅第。这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丹房的门拍打不开,又转向那个两层木楼。被惊醒的主人在窗洞上探一下身,书童出来了。
我一个人待在了那间冷冷的厅堂里。今夜曼陀罗的气味比任何时候都浓。我的头抵紧了大床,让叠起的蜡染花布把鼻孔堵塞起来。沉沉夯地的脚步声响起来,宛若大炮轰鸣。灯亮了,进来的人默立一旁。我抬起头,第一眼看到的又是那肥厚弯曲的上唇、散淡空洞的大眼。
5
自那次凌晨造访之后,我有了十多天平静的时光。这期间偶有躁动,也总被一些日常琐屑压制和冲淡了。一天傍晚,管家肖耘雨不无神秘地压低声音告诉我:徐竟着人来取一笔银两,数目不大,但时间紧迫。我略有迟疑,他就稍稍提高声音说:“老爷在世那会儿这只算一个小零头了。”我知道这是送给革命党人的,并无疼惜,只是听到“徐竟”两个字心头一热。我和兄长有太多时日没有见面了。
我与管家商量了实业事宜。关于警匪诸项,我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准许府里将少量银两送予海防营的人,但要在他们真正出手相助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按捺不住火气,因为一个仆人不小心跌伤了手臂,府上竟然将其送到了那个教会医院。尽管这人在短期内痊愈了,也还是让我心中愤愤。
已经许久没有去那个人的丹房了,当然是极力忍耐的结果。我常常将自己看作一只身陷罗网的小兽,血迹斑斑遍体勒痕,却能一次又一次挣脱。某种熟悉的焦渴总在喉部那儿汇拢,然后弥散到全身,像炭火般炙得我坐卧不宁。我预感这段平静期过去之后,一只翻毛刺刺的野兽又会在原野上出没。我隐隐觉得:正在施行的这一切不过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
府内的时光变得漫长了。为了驱除日常的庸碌和厌烦,我琢磨着怎样有所作为。一连多天去酿酒公司的地下酒窖,对蜿蜒百步的贮桶长廊深感兴奋,陡然意识到祖上产业日日累积之功,这当中凝聚了多少心智与汗水。这期间经历行业倾轧、世事变异、革新与守旧,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平坦。特别是西洋技法之引进,从曾祖父开始的古老程式被一一废弃,当是父亲的至大功勋。他能够重用海外归来的技工,耐心听着对方咕噜噜吐出的洋文,欣赏最时新的彩色酒标,终于成为半岛地区的时新人物。
站在地下长廊中感受一阵阵凉爽,想象当年父亲踏着这里的石板往前,伸手抚摸橡木桶的样子。他认同酿酒师的言说,相信在时光中慢慢酿化的酒浆是有生命的,“它们是隐伏的精灵。”他说。我想未来的一天,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或者是苟活的清廷,只要战乱一过,这地下长廊又可拓出百步。一个伟大的前景鼓舞着我,觉得未来的一切并非虚妄。我在府邸中走动,发现攀缘植物充斥了每个阴湿的角落,黑苍苍的建筑实在太拥挤了,缺少几个稍稍开敞的花园。所有树木蓊郁的地方都是寄生植物的天堂。我端量着几代人造就的格局,设想日后的改易:拓宽甬道,辟出空地,还要加盖麒麟医院那样的新式楼房。我登上那座石头碉楼时脚步放得轻轻,生怕惊动了沉伏于此的灵魂。我甚至认为曾祖父和祖父仍会不时地光顾这里,在深夜里捣弄一个个心爱的器皿。我摸了摸坩埚,嫌烫似的倏然抽手,虽然它已经熄灭了一百多年。
我吩咐车夫备车。朱兰好奇的大眼睛看看我,只一会儿就提来一只小巧的食盒。马车已经待在南门,车夫手持长鞭站立在全城最奢华的车子跟前,目不斜视,待我和朱兰走近,立刻上前一步撩开厢帘。坐定后我才告知:去城里转转,沿着青石街往前,到东河后再绕向西大街的闹市区。
以前常有这样的周游,朱兰正好趁机买回一些东西。她坐在车中满脸欣悦,大概想起了过世的老爷领我们游玩的情景。还是同一辆车子辘辘前行,可转眼已物是人非。眼前的街市有些萧条,行人衣衫破旧,神情不爽。巡街的兵丁排成一队,挎刀并背一杆火铳,已经是新军装束了。车子沿河往前,渐渐飘来浓浓的淤泥和腐草味儿。再往前就该是那片滩涂了,那里多次用作刑场砍杀革命党人,看客围得水泄不通。我让车夫改道。
街道变窄,人气稠密了一些。车轮碾着坑坑洼洼的路石,不时有一下剧烈的颠簸。我看着外面的摊子和人流,将帘子掀开一道缝隙。几个女子在卖彩线的摊前围拢,我的目光很快被其中的一个吸住。心跳在那一会儿仿佛停住,因为那只熟悉的手摘下肩上的挎包,正掏出一束彩线与摊子上的对比。她高高兴兴买下来,推拥着一边的女伴。车子就要驶开,我让车夫停下。行人好奇地注视车子,我却一直看着那个彩线摊前的女子。
她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说一句“稍等”,就跳下了车子。前面是四个女子,她们扳肩搂腰亲热极了,相互比看新买的彩线,其他全不在意。我真想寻个机会喊一声,还是忍住了,只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们艳丽的服饰、飘起的发辫。她们拐进了一条巷子。我加快几步追上,却不见了她们的身影。
巷子里有三个胡同,我在中间徘徊。有个拐角写了“小白花胡同”,我站住了。这儿青石铺就,石缝里长出几枝打破碗花。胡同深处传来了清脆的笑语,让人心里一阵发热。
从胡同走出,阳光刺目。朱兰正站在巷口等我。
6
一连多天都在书库中折腾,身上挂满了尘埃,像肺痨病人那样巨咳,泪水涟涟。这些老旧书籍是多年封存的部分,早在祖父时期就被列为禁书,父亲有几次差点把它们一把火烧了。我在整理典籍时第一次打开了这间被遗弃的屋子,迈人的第一步就被呛了一口。好像酸腐中透着恶臭,让我疑心有一两只老鼠死在里面。后来我从木匣和锡盒中取出了一些霉变的残页,有的是烂掉了半卷的绢或纸,这才明白邪臭之源。它们是秘藏的养生古卷,甚至可以判为躲过了多次焚书的遗物,或许还是几千年前远去咸阳、最后被秦始皇坑杀的那些倒霉方士的东西。这些帛与简、麻纸,几经抄写装订,显然耗去了不止一代人的心血,可能这才是阻止父亲毁掉它们的原因。他在最后一刻动了‘恻隐之心。但他在后来还是不忘叮嘱一句:远离这间屋子。
这是一间密室。我发现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即便花上最大的耐心也无法通读,它们很可能要留给某些专门人士。这些古老的文字十之八九涉及房中秘术或灵符咒语之类,烦琐的记载玄虚而又缜密,相信能够诠释者在半岛地区已经绝迹。其中的一小部分借助近代印刷术保存下来,配有插图,某些局部实在撩拨人心,令人于蹙眉攒额间心旌摇动。那些符咒使人将信将疑,艰涩到无法卒读。我几年前匆匆为之造册,然后照旧封藏,再也没有开启一次。
为了驱除死鼠气味,我洒上了双倍的花精水。我算不得一个积学覃思之士,只想印证一个判断:邱琪芝的用心和秘术源流。我不得不再次面对这里的恶臭和令人愤怒的艰涩,相信这无法解读的缘由多半出于著者的阴邪,他们当中混有不少骗子和淫棍,个个骄奢淫逸,荒诞不经。
几天过去,我先是头昏脑涨,接着恶心胸闷,不得不中断阅读。就此我更加相信父亲封存它们的理由。我在阵阵花精水和恶臭掺杂的黑屋中自问:一个人究竟要将体内的魔鬼紧紧闭锁,还是将其驱逐?结论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冷酷无情地放逐它。
夜晚再次变得漫长了。有几次我伏在窗前做沉细悠长的呼吸,尽可能弃绝意念。可是这样一会儿即有灿亮的火花在啪啪闪动,睁开眼睛时,它又消逝了。原来它来自不宁的内心。
整整一天无所事事。我又想到了邱琪芝的丹房,一直在屋里徘徊。当西边挂满了火烧云时,我走出庭院,穿过稠密的林子,打开了沉沉的角门。开阔的街区上行人匆忙,他们都急着回家。我在一间挂了蝈蝈笼的布店门前站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我被一个即将收起的摊子吸引,走近了眼前一亮:这正是卖彩线的地方!我急急抬头遥望,看到了对面那个巷子,它在晚霞中泛出了火红色。这样伫立了一会儿,像被一只手牵拉着,一直穿过了大街。
小白花胡同静静的。站在一个黑紫色的门前,看着门板上紊乱的划痕,心噗噗跳起来。门虚掩着,我敲了几下,然后鼓鼓勇气推开。一个栽了石榴的青石小院里拉着几道绳索,上面晾晒着五颜六色的布,中间一个瘦瘦的姑娘,见了我一愣。“我来找一个熟人,一个朋友。”我向她打着手势。她马上明白过来,反身回屋,出来时和三个姑娘一块儿挤在门口。要找的那个女子却不在其中。那个瘦瘦的姑娘又一次回到屋里,再次出来时挽着一个人,正是“酒窝”。我们的目光碰了一下,发现她有些慌张。我上前一步,她却做出一个手势,拒绝我走近。
几个女子一阵哄笑,“酒窝”回到了屋里。我在院里僵着,不知怎样才好。大约过了十多分钟,“酒窝”终于出来了。她肩上挂了那个熟悉的挎包,引我走出小院。天色暗下来,我们在街上一家关门的店铺前站住,抚摸了一会儿门边光滑的石狮。显而易见,她也打不定主意到哪里去。这样犹豫了一会儿,她牵牵我的手,从另一条巷子穿出去。我们走啊走啊,一会儿闻到了青生生的气息,前边是一片空地,到处长满藤蔓植物。
我们试图坐下,可藤蔓下全是瓦砾。只好继续往前。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竟然走得飞快,不时停下来等我。后来她干脆牵上我的手。我们在一片红薯地坐下来。我拉住她的手试一下自己的心跳,她收回手即比画起来。我无法在夜色里看清她的手语。红薯蔓在脚下纵横交错,我折了一条蔓子缠上她的手足,她发出了快意的笑声。她把一双手放在近而又近的地方比画着,我好不容易才看清:
“你是我的贵公子!”
7
那个夜晚我们在红薯地里待到月亮升起,一起迎来了难忘的明媚时光。露水打湿了衣衫,她的眼睛宛若星星。下半夜有蝈蝈在近旁呜叫,饥饿感阵阵袭来。她伸手从地下挖出刚刚生成的红薯,两人一块儿咀嚼。这个月圆之夜没有风,红薯叶在银光下泛着明暗相间的颜色,像一群伏下的鸽子。她不顾一切地亲吻我,我好像第一次发现这张嘴巴开阔而柔软。
远处有雄鸡啼叫,天色仍旧暗淡。月亮隐去,黎明前的凉意弥漫开来。她让我的手感受她噗噗跳动的心房,然后仔细地系好上衣,搓了搓脸,捏了捏我的鼻子站起来。我离开前发现腰上的一只玉坠不见了,伏下身子细细寻觅,还是不得。
那个夜晚让我记住了一个新鲜而又俗气的称谓:贵公子。我每当这样悄声呼叫时就会想起那张开阔的大嘴,它是那么诱人。我实在无法在她浑身洋溢的青生气息里保持一颗冷漠的心。我有一次鬼使神差地对朱兰说了一句:“贵公子。”“什么?老爷!”我回过神来,摇摇头。我一静下来就要走神,它已经飞到了小白花胡同。
我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季府还是邱琪芝的宅第,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无法安顿自己。我已经不思茶饭,这让朱兰忧虑。她最后竟将我的窘境告诉了管家,他在我身边默默站了一会儿,镜片里的双眼更加阴沉和沮丧。我取出丹丸,在他们的注视下吞服了。
许久以来我总是按邱琪芝的指导,任由气息自行流转。可是这一次身体处于飘摇的状态,好像肉体空前地没有重量,甚至失去了笔直向下的力量。身体仿佛像气体一样聚聚散散,又好像随时都在漂移的无舵之船。丹丸在腹中融化,渐渐变为细小的火苗,顺着脉管蔓延到四肢。朱兰为我端来了凉水,我一口气饮了几大杯,吃了一点粥食,然后躺下。我什么都不再想,害怕蛮横的意念会乘虚而入。“老爷,三天了,你只吃了半碗粥。”朱兰带着哭腔说。我反驳说:“不,我从来没忘丹丸。还有,你给我的是蜜水。”
这天半下午我爬起来,觉得全身异常轻盈,就试着走出屋子。庭院里有一棵结籽的马兰,我蹲下看了许久,站起时竟差点跌倒。朱兰惊呼着过来搀扶,我摆摆手。两腿像踏在云朵之上,一直飘出了门廊,又出了府邸。朱兰泪眼潸潸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我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可是眼前的人流花花绿绿淌了一会儿,嗡嗡群蜂似的喧嚣过去,接着就安静了。我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小白花胡同里。一种归来的温馨扑面而来,我熟练地推开了那扇紫黑色的小门……
我不知睡了多久,好像一次还清了二十多年的困债。蒙咙中听到姑娘们小心翼翼地走动,然后是哨声议论:“都日上三竿了。”“那个睡呀,打鼾呢。”“睁开血丝大眼了,然后又睡了。”
醒来后,只有一个叫“秋月”的在屋里,其他人都上街去了。她站到近旁说:“你送白菊的大玉坠儿真好,能送我一个吗?”
我马上明白这是红薯田里丢失的东西。原来是被“酒窝”取走了。她耸动着问我能不能,我随口答:“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