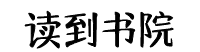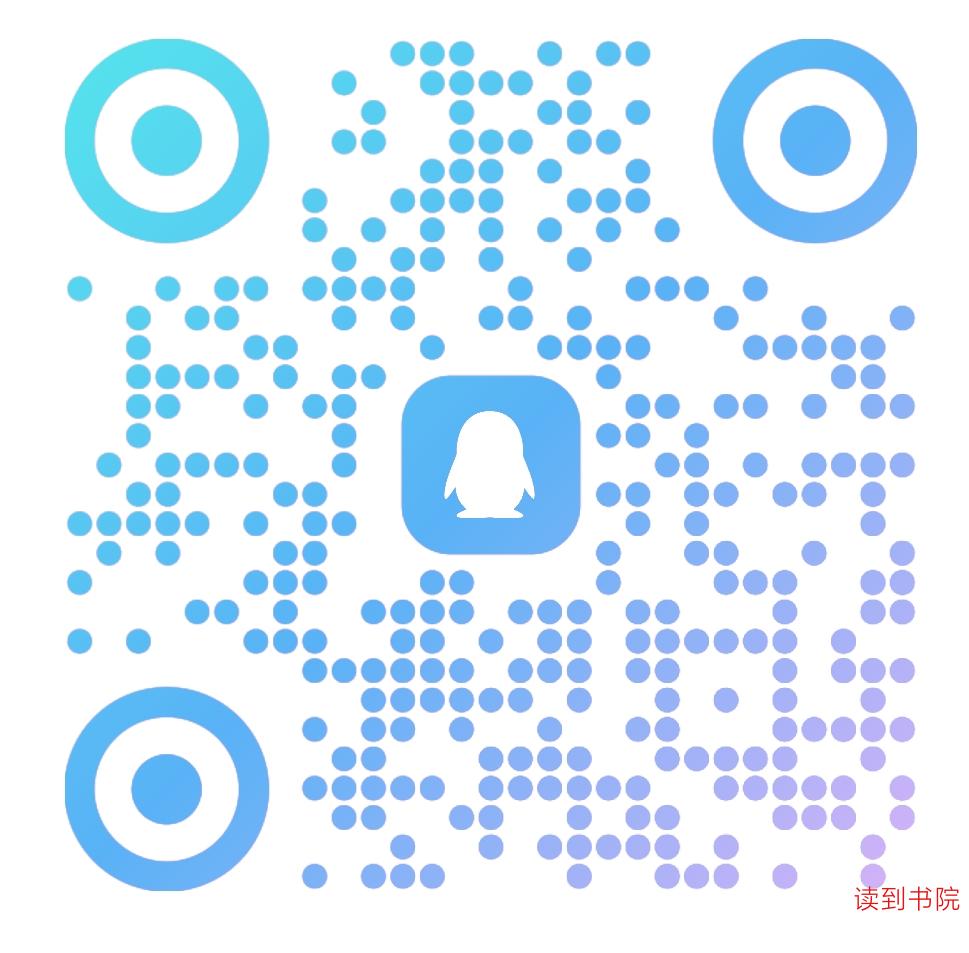1
那是个异常紧张的黎明。我们与伊普特诸人仔细确定了一些事情的细部,又一起去顾先生处告别。院方用汽车送顾、金二人出城。我嘱司机将自己的车开回,然后换上那辆马车于院外待命。时间已经不多了,按计划院方派去告案的人已离开了一会儿。我和伊普特院长及陶文贝一起等候。这是院长室。我向主人讨一杯茶,伊普特说“对不起”。他和陶文贝一起张罗茶水,手有些抖。刚刚饮了两杯,静谧被打破了。可以听到杂乱慌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陶文贝眼中含泪。我看看她,又转向伊普特:“没有什么,院长先生,他侵犯了陶文贝,就必得去死。”
他们到了。刀,火铳,新军服装色泽逼人。令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府衙的兵士,而是海防营的人。领头的是副协领,自称见过季府老爷。他们一边询问一边记下,将我和医院的人分开。副协领出去了很长时间,回来时笑吟吟地对我说:“老爷好身手,咱请吧?”我没有上他的车,而是直接走向那辆在早霞中闪着华丽光泽的车。我的车夫持鞭肃立,灰色马浑身油亮。副协领与我一起登车。
我在车上再次申明:万不可扰烦院方,此事与他们无关。副协领点头:“问个口讯就没事了,老爷不必替洋人操心。”
车子驶入海防营的领地。这里比想象的深邃,直驶了很长时间才来到一个院落。就在这儿,副协领又离去了好一会儿,回来后让车子继续往前。前面又是一道大门,里面全是低矮的旧屋,一律镶了铁棂,戒备森严。这让我想到了一座监所。车子在矮屋中拐来拐去,最后停下。一排挎刀持枪的兵士站了一溜。副协领先下车,然后殷勤地请我下来。“这是什么地方?”“哦咦,当然比不上季府了,全是陋室,给季老爷备下的还是最好的一间哩。”
打开的屋子令我皱眉。腐烂气息直冲鼻孔,墙壁多有漏水印迹。小小的一间屋子里只有一张八仙桌和一张窄床。屋角有一只便桶。竟然没有净手的器具。“咱们进屋说话?”副协领在门口摊着手。我走进去。由于只有一把方炜凳,他只好站立。我说:“请为我禀报一下,就说季府有人拜见康永德大人。”“在下一定禀报。”
门被锁住。我一个人关在了屋里。看着粗粗的铁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陷囹圄。“嗯,好嘛,季府老爷来到了这样的地方。”我看着铁棂上垂下的一只蜘蛛,看了很久。太阳升到半空,云朵从远山驶出。微风透人,霉味稍减。我想象那惊心一幕:自己的手在那个时刻扼住了那个人,迅猛一扭,千钧之力尽发。是的,既然这家伙的脏爪触到了她,那就真的该死,不容商量。
我好像真的做过了一生中的大事,稍感轻松地在窄窄的室内踱步。我发现屋后还有一个小窗,也装有铁棂,透过它可以望到一丛低矮的竹子。
午餐时间到了。提来的竟是小半桶粥食:稀汤寡水,透着馊气。不可食。
在那个康大人到来之前我想静坐一会儿。这里除了气息恶劣,还算清闲。我一闭眼想到的竟是初次见到邱琪芝的那个草寮。这个古怪阴谲之人久已不见,这会儿竟在意念深处浮现出来。我站起,再次看后窗的碧竹。好生可爱,可惜长在了此地。
天色渐晚,又来半桶稀稀的粥食。我未动一匙。天完全黑下来。我站在窗前等待一天繁星,等到了疏疏的几颗。再等,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喊叫。是撕裂心肺的呼号,还有辱骂与鞭杖。这里原来是刑讯之地,实在可怕。随着夜色深入,凉气也浓,我紧了紧衣服。有一盏大大的灯笼在移近,脚步声告诉我来人了。门哗啦一声打开,进来三个人。为首者是个稍胖的家伙,眼皮沉重,只余一道小小缝隙看我、看屋子。随员说这是总兵大人。我坐在凳子上未动。有人搬来一把圈椅给总兵大人。
“委屈季府老爷了,想不到我们在此会面。久闻大名,未能去府上拜见。事已至此,实在可叹……听说季先生好身手。”总兵边说边上下打量我。
我没有看他:“胆敢碰我的女人,也算活该如此。”
总兵一手抓紧扶手站起:“季先生可知所杀何人?”
“一个醉酒商人嘛。”
“哪里啊!季先生,让我告诉你吧,这个人是巡抚大人、太子少保派来的道员!”
2
总兵在屋内急急走动,捻须,不时看我一眼。我连表讶异,心里想的是金水的话,此刻开始钦佩他的机敏。我问:“既是太子少保身边道员,为何做下这等龌龊?”总兵不答。他踱了一会儿,在我身边站住,声音低下来:“我来问你,另一道员死于谁手?”“还有一个?”“先生真的不知?”“处置这一个就够麻烦了,还有一个?”
总兵坐到椅子上,好像倦怠了。有人附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站到粥桶跟前嗅了嗅,怒斥:“换食盒来。”粥桶提走,一会儿提来了一个不大的食盒,打开后香气四溢:两荤一素一汤。送饭人将饭菜一一摆到八仙桌上。我没有礼让,实在饿了。
总兵一直待我餐毕,挥挥手让身边的人退下。只我们两人了。他叹气,磕牙,摇摇头,“季老爷想必有所耳闻,贵府中有人串通乱党,闹得凶蛮,罪不容诛啊!”我站起:“岂有此事!大人言重了,季府祖辈持守之信条,即远避各路纷争!我再昏聩无能,也不至全然失察……”他愣愣地看我,怔了一会儿,突然将手伸到灯下,屈起了一根指头。我马上明白这是说管家那个断指儿子,佯装不解。他说出了名字。我“哦”了一声:“原来说他!管家早就将这个孽子逐出家门了。不过据我所知与之来往者无非赌徒逸少,绝非乱党。”
总兵眯上眼回到座位,“果真这样倒也无碍,只怕不唯如此吧!”
“空口无凭,以后只要拿了,审他便是。你说那个人与季府早无干系。”
外面又传来犯人呼叫。总兵扬脸哼了一声,有人端来热茶。我们饮茶,暂时无话。兵营的茶以前也领教过,浓,苦,只能小口啜饮。这让我想起去北马那次的苦饮。季府的香茗在这里是找不到的。我暗自揣摩对方的心思路径,担心他们得知道员被杀后即做好了准备,故意让我待在这个脏陋处听夜审哀号。一切皆有用心。或许他们会将医院的人关在另一处,这一念让我额上渗出汗粒。既然整个事件起于那个南方女子的一路追踪,那么最后的重点一定会落在顾先生和金水身上。果然,总兵很快将话题切近:
“你的老朋友还好吗?我是说那个顾老板。”
“还好,治过眼疾后出院了。”
总兵磕牙,这是他运思的习惯动作,“说来也巧,我这里接到的密报是,南方乱党首领中也有一个半瞎的家伙。”
“那真是太巧了。不过有眼疾者越来越多了,乱世不光折磨人心,还折磨眼睛。”
总兵哈哈大笑,站起,说改日再聊吧。他对门口的兵士说要好好侍奉季老爷,然后回首抱了抱拳。
这家伙离开后我才想起了康永德,想这人迟迟不见的原因。这会儿从头将总兵的话一一滤过,从中寻觅玄机。颇费脑力,近乎猜谜。这个冰凉的秋夜想着父亲:正是他让季府走近了革命党。家族与人生啊,认命而已。
静坐总被不远处的哀声所扰,未免沮丧。按时服用丹丸。无思欲无念想,任由气息周流。那个阴郁的导师无处不在,令我气恼。一遍遍想着那个滚烫的面容:陶文贝。此番动荡如若伤到她一丝一毫,都将是一生难赎的罪恶。一个“赎”字又让我想起了朱兰。但愿她们都安然无恙。女子皆为世间妙物,让神灵护佑她们吧。
入睡前照例要如厕。这个脏臭破旧、无坐垫无封盖、边缘参差如镞的便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奇物。因为生来第一次见到这等拙陋,让我好好研究了一番。小解好说,大解为了不伤及臀部,须取马步,那是一种功夫:季府的螳螂拳师们个个都有极深的马步站功。
3
一天无事。茶饭皆好。入夜的灯笼渐行渐近,那个总兵又到了。当阵阵哀号戛然而止的一刻,灯笼正好抵达门口。这次入门仅总兵一人,他抱拳,入座,默默无语。我破例为他斟茶,他以单指叩桌示礼,仍旧无言。这样过了半晌他长长叹出一声,抹了一下眼睛。仔细看看灯下的人面容哀伤,却无泪痕。我问:“总兵大人为何不快?”他再次叹气,站起,踱了几步又坐下:“季老爷在下失礼!实言相告,我不过是水师营教官,这些天代总兵行事而已,如今再也不敢相瞒……”“还有这等怪事?”“是这样,总兵性子暴烈,我担心他冒犯老爷,就代他先行来见,许诺定会劝解功成……想不到他好生性急,已回禀巡抚,今个斩令下来了。”他站起,一瞬间涕泪垂落。
我觉得一股灼流从头顶淌下,淹没全身。随即没了痛感与思绪。眼前的人一边揩泪一边摘下顶戴。我全身重量移至两臂,支撑着才没有伏倒在桌上。“你再说一遍。”我盯住夜色。他复述了一次。“斩令”二字清晰无误。
“他是太子少保身边道员啊!”他这时涕泪全无,“季先生正值盛年,何不供出一人顶罪?万万不可游移了!”
我强忍隆鸣如雷的心跳,问:“那该供出何人?”
“这就由季老爷定夺了,原是不难的。”
我不再应答,闭上眼睛。一股麝香味儿弥漫过来,睁开眼,见他双手奉上一只寿桃状的香囊:“这屋子秽气太重。”我像他那样单指叩一下桌面,他将囊放下。“季老爷三思啊!按律法今夜就得佩戴刑具了,在下泣求,这才应允最后那会儿再、再……嗯,那会儿再为老爷戴上。”
“刑具在哪里?”
“就在外边了。”他仰脸瞥瞥门口,击掌三下。
两个兵士脚步重重地踏进来,把几件黑乎乎的东西噼噼啪啪放到地上。二人退出,他将灯笼移近,让我看清这副木头夹板,外加锈迹斑斑的手锁和脚链。它们将室外的寒凉一起携来了,这会儿身上一阵巨冷。我蹲下看着,问:“上路又是哪一天?”“这得看总兵的脾气了。在他那儿不是什么大事,朱笔一勾,报给巡抚就算结了。”“这在季府那儿也实在算不得大事。”我答道。他像被烫了一下,身体一颤:“难道你主意已定?行前没话?不想见几个人?”“自然要见。”“那你……写下来吧。”他额上出汗了。
有人取来纸笔。我写下“陶文贝、朱兰、管家、康永德”四个名字,想了想,划掉了最后一个。
一夜无眠,窗外传来时断时续的哀号,间或还有秋虫的鸣声。秋虫和人谁更从容?想不明白。我爬起掌灯,移近了看那副刑具,不知因为绝望还是陡生滑稽,只想发笑。但笑声未出,一行泪水早顺着鼻侧淌下。我躺在床上想:以前曾说为了陶文贝可以去死,而今竟然真的应验了。人哪,大话慎出。
黎明时我于后窗那儿徘徊,渐渐凝神:一丛竹叶下有一只完美精巧的鸟巢,开口处正探出黄口小雏。啊,是织巢鸟,真是令人怜惜到极点。我抵紧了窗户看着,惊异于前一个白天竟毫无察觉。原来人在特殊的时刻才最能把目光投向弱小。
就因为织巢鸟,我这个早晨少了一些悲绝,甚至有了一点儿时的欢娱。早餐只饮一点稀粥,然后等待阳光。
窗户变得眩目时,管家和朱兰来了。两人相互搀扶着,进门时还是差点跌倒。管家泣诉:“肯定是那个孽子牵累了老爷,我们父子真该以死抵罪!”我厉声喝止,让他站好。他扶着桌子才立住,浑身仍旧颤抖。我说:“府里的事情你好好打理吧,一如既往,有事情找朱兰商量。”管家泣不成声,只是点头。朱兰嗓子已哑,可能一路上哭坏了。她急急打着手语:“这怎么会?老爷,我们这就去找康大人!”我告诉她:“不用了,他能来早就来了。”
“怎么会!怎么会!老爷啊!”管家喊叫起来,我再次喝止他。
4
陶文贝没有来。我心急如焚。我必须知道她的安危。又是一天过去,这一天没有任何人造访。白天没有哀号,入夜则要响起,直到凌晨。抵御这可怕的焦灼也唯有“遥思”了,死亡之后可谓至遥,那是未知之境,远在星汉渺茫处。心系那片无尽的黑色会有一种翩然飞去的感觉,十分奇妙。我曾琢磨“仙化”与“死亡”之别,发现二者纠扯难分。相同处是都要挣脱人世,相异处是最后一刻的欣然与恐惧:如果我带着初识织巢鸟那样的欢娱离去,不就成了家族中第三位“仙化”者吗?想到此浑身一阵灼热,激动不已。
因为睡不着,静坐也屡屡失败,就花了许多时间去研究那副刑具。以前只从穿街的犯人身上远远见过,而今近得可以抚摸了。锈铁泛着腥气,那木枷由槐木或榉木做成,又沉又黑,中间贴颈的圆洞透出酽色,摸一下极脏腻。这脏腻令我不快的心情持续良久,对它的厌恶甚至超过了死亡。如果换一副灵巧的新枷则要好得多。我站起注视,突然闪过一念:自己也许不会很快上路的,因为这脏臭的刑具与我同处一室,就是最残酷的责罚了。
黎明时刚刚打个瞌睡,送食盒的兵士又把人惊醒了。不记得昨夜吃过东西。今晨口苦异常,那糕饼每嚼一口都难以下咽,像是黄连做成的。果然,它的下泻功效很快显现,我不得不在马桶那儿练一会儿马步了。奇异的恶臭,大概集起了全部的冤仇与困窘,还有恐惧和厌烦,这会儿一起泻下。我差不多要昏厥了。如此一来,身上倒也轻松了许多。
那个混蛋昨夜将香囊取走,我这会儿只好忍受浊臭。有人笃笃敲门,门开了,侧立在那儿的一幕疑是怪梦:一根马尾辫垂下,缓缓转身,是邱琪芝!我忽一下站起……他掩住口鼻进来,四面环顾,最后抵墙而立。“我心口两次痛醒,就忍不住去了府上……费了好大周折才进来。我的天。”泪滴从他紧闭的双眼渗出,唰唰成串,难以止息。
这是我近四年来第一次见到他。容颜未变,还是那么细嫩。这个人真的不会衰老。我想不到会在这样尴尬的时刻与之会面,哀伤无以复加。一切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最后了,我想听前辈一句真话,您和我父亲到底为什么分手?”
“好吧。这个时候了,为师的告诉你:他是革命党。”
我身上一阵寒战。我咬紧牙关又问:“你害怕牵累?”
他微眯双眼:“在我这里,养生与革命水火不容。”
“可是家国朽败.民不聊生,我父亲也是迫不得已。”
“府吏衙门全都一样,都是人,人不变,怎么折腾都没用,白白流血而已。人如果活上百年,就会看到终究一样。所以人生在世,唯有养生。”
我想起了王保鹤先生的“教化”与“革命”论,觉得二人或有相似之处。不过即便是王保鹤,也仍是北方支部的人。可见人生必得兼顾眼前,于利害权衡中择其善者。
“既然白白流血,为什么要做?你来回答!”邱琪芝又逼近一句。
“那当然不能做。不过也许不会白白……”
“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只变了个江山名号,最后全都一样甚至较前更坏,这难道不是人间大恶?你觉得不会,那是活得太短。”
我远不足百岁,所以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
“无论采用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就是扬罪恶。”他一言以蔽之,站到窗前。待他转身时,又见两行长泪。他正为我而悲。他用力揩去泪滴,换个轻松的话题:
“几年了,为师的想念啊!你禁欲闭关那些时日,有什么心得?”
“我……啊,还记得您说高人之气,那么它到底在哪里?”我终于记起了一个切近而又具体的问题。
“喏,这儿,”他拍拍脚踝,“气沉于踵,踵随气行。你当知不倒翁的原理,它怎么也不倒,就因为重量全在下边。”
“明白了。我想说,修持诸法中,最难行的就是‘遥思’了;而最遥远的不过是死亡,那才归于彻底的安静,无欲无念。”
“这是极而言之吧。不过为心上人去死还差不多;为仇人,为家国,那都算不得有多么遥远!”
我站起来,直视这个面色如婴孩般鲜嫩的人,只想直言相告:“啊,真的是一语中的,豁然开朗,我这一次就是为了心上人去死啊!”
5
整整一个白天和夜晚都处于激越和感念之中。我与邱琪芝的会面带来了新的印证与觉悟,尽管这已经太迟了。不过也只有此刻,我才能领会什么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是的,别过至亲,别过导师,此一去遥遥无期。唯一的遗憾还是那个秘传独方:我死或不足惜,可叹的是广陵绝响。
我为最后一念折磨,心有不甘。想啊想啊,眼前闪过一个个面容,最后凝视着深棕色绒帽下的一对美目:“朱兰!”
怎样将独方授予她,令我苦苦琢磨,在屋里徘徊。时间分分秒秒流逝,焦虑逼人。我向兵士索要笔墨,再次写下求见府上仆人朱兰。两天过去,没有一点声息。第三天上午令人绝望,吞了几口苦食躺在床上。我记起昨日丹丸还没有服,又起来找出那个小瓶:只有五粒了。
黄昏时分铁门洞开,一个衙役模样的人进来,身上没有挎刀,双手抱拳说:“季老爷请吧!”朦胧间觉得这是催我上路,双耳轰鸣,心跳如鼓。瞥瞥窗外日光,时辰不对,再端量面前的人,一脸谦恭:“我家老爷请您小酌,也算讨教,请吧!”他又说了一遍。我这才看到门前停了一抬轿子,几个轿夫站在那儿。
我坐在轿中百思不解,只任其一路轻颠。出了监房不远即钻入巷子,拐来拐去,最后竟进了一座朱柱灰墙大院,这儿林木蓊郁,估计是哪位侯爷的宅邸。下轿后有一老仆迎候,陪同的那个衙役紧跟一旁。高高的台阶上站了一个又胖又矮的人,五十多岁,笑容可掬,正居高临下看着,见我开始登阶即转身进屋。
屋里是空的,只有镶了螺钿的硬木桌椅,案上还摆了几碟瓜果。进入内室才见那个胖胖的人坐在席上,向我微微点头。“这是老爷!”老仆躬腰说。“季府先生?”胖子并未起立,只让我坐到对面。酒食颇丰,香气扑鼻。所有人都退下了。胖子笑着,嘴里“啊啊哦哦”。他身上挂了不少玉佩,手中还转着两颗核桃。从进门那一刻他就一直留心看着,这会儿点头抿嘴,咂咂舌头:“先生奇人!老夫三生有幸啊!”我不知端的。“昨日听说先生进来了,真是机缘天造!我说,会会也!”
“进来”二字说得轻巧,我觉得此人稍稍有趣。这人容貌庸常,看上去非文非武。他笑眯眯探头:“先生可谓道中异人,请你来说说方术。我本是性急的人。来来,先饮几杯嘛。”他敬酒并一口饮下,我只抿了一点。“老夫百事不喜,只求长生,搜罗不少人间奇方哩。”他连饮几杯,很快脸色红涨,人也更加和蔼。我说:“愿听指教。”他一仰脖子:“哪里,季府丹丸我也尝过。你看,”他攥拳举臂,“我像多大年纪的人?”“三十多岁吧!”他哈哈大笑:“哧,老夫五十有二了……”
整个席间胖子自斟自饮,大口吞食,后来发现我并不动箸,就指着菜肴:“吃!”我吃了一点,他高兴了,小声说:“有人献来异方,说来忒简单,不过是采来春天的野兔屎,每天五粒代茶饮……”我怀疑听错,待他再说一遍,差点笑喷。“阁下以为如何?”他不无得意地盯住我。我说:“民间验方嘛,我想那野兔品尝百草,必有奇功。”这一回答令他很快兴奋起来,随即大饮一口,拍打膝盖唱道:“我也曾、在山冈、追赶野兔……”唱罢又附上耳边:“春季的野兔屎最好,夏秋次之,冬天则不可采。”我点头:“不可采。”
他已经半醉了,在我全无预料时竞解了腰带,一定让我看看下体。我躲开一点,他以命令的口气说:“但看无妨。”我只好瞥上一眼,见那里勒紧了一根红色布条,吃了一惊。“嗯,这也是一个秘方了,每天勒上半个时辰,可收奇效。阁下以为如何?”我待他束好腰带,一边想着怎样回应。我说:“也许不错,这也算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他大笑起来,连连碰杯畅饮。这样高兴了一会儿,他突然瘪瘪嘴巴:“我刚刚传了你两个秘方,你哩?该不会把自己的秘方全都带走吧?带走何益?”
我至此算是明白了他的用意,四个字即可概括:趁火打劫。我心里冷笑,口中却愿与之交换:“我想用这个独方换回一条命,不知阁下可能办到?”
他立刻慌促摆手:“使不得!这是巡抚、太子少保督办的要案……”
“那就只好免谈了。”
“啊呀!啊呀!你带走它又有何益?”他急得搓手顿足,离开桌子走动,哭丧着脸立在面前,“我为先生备下美酒吃物大宗,还有更多银子。阁下!阁下……”
要搪塞这家伙原本容易,随手写下几味“人参”“茯苓”“桑葚”之类也就打发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矜持一些,剪手踱步许久,很像最终下了一个决心,对他说:
“也罢,念你一片诚心。不过那些吃物和银子也就算了,就为我准备一个上好的马桶吧。”
6
我终得免除马步之苦。安坐马桶这段时间正好用来回想那个胖爵爷,想他的秘传异方,忍俊不禁。而站起来之后却是双倍的焦灼,是无法忍耐的企盼。我深悔上次朱兰和管家探望时竟忘了一件大事:怎样传下那个独方。
陶文贝仍无踪影。我曾对水师教官和副协领分别提到西医院,着重指出整个案情与他们无关。听者讪笑,然后回我“勿操洋心”。可是一想到陶文贝即有揪心之痛,觉得失去的所有光阴太过可惜,我像个梦游人一样恍恍惚惚走到今日,两手空空。正因为没有她不可度日,也就再无多少日子可度,看来真是命该如此。我只想再写一封长信,与她做最后的诉别。
我一一回述两人一起的时光,把黄金铸成的分分秒秒重温和拉长,永不间断。我不敢使用夸张的口吻,担心她从中看出我的虚荣。除了在窄逼的车厢内因颠簸而挨近她的身体,我们两人不曾有任何机会触碰过。令我奇怪的是,好像我们也没有过礼节性的握手:那种洋人礼法是多么好的东西。我总是抱拳。我甚至在偷窥中都要微眯双目,也正是关于“目色”方面的严格训练,让我习惯了谦卑含蓄地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美好,而绝不会因攫取的急切而吓走对方。或许就由于这无形无迹的微妙吸纳,我的体内已包含了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艳和力量。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卑微污浊的生命而言,该是多么巨大的支持,也正是这支持使我有勇气在那个关键时刻做出了决意:为了她,我将承担全部后果。
这封信太长了,并且还要一直写下去,直到地上那摊刑具将我的双手缚住。一支笔从容向前,似乎永无终止,直到守门的兵士哗啦啦将门打开。
尽管是逆光,我还是被门口的剪影惊得站起,心跳险些停止。这不是梦,然而无数的梦想加在一起的美好和欣喜也不过如此:陶文贝真的来了。
这个让我日夜牵挂思念的人完好无损地站在跟前,一切都不需忧愁,一切都悉数完成了。我小声自语道:“起义成功了。”“你,你说什么?”“啊,一句梦话。”泪水从她脸上噗噗流下,她想尽最大努力止住泣哭却不能够。我问起了她和伊普特院长,还有艾琳和雅西。“他们都好,大家都好。不过谁都不准来这里,直到最后我才被应允了,因为……”她哭出了声音。
“因为什么?”
“因为你对他们说过,我是你的……女人!”
我低下头:“对不起,那是我宰杀这个畜生的唯一理由。”
“我明白。我没有生气。可是,可是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你?你是季府老爷啊!”
对她做任何解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来了,她站在面前。
7
原来我走后还发生了许多事情。巡防营并没有放过麒麟医院,他们将长廊西端的一半隔离开来,让所有参与顾先生治疗的人全待在里面,实际上成为一处临时禁所。雅西和伊普特院长被分别审问,艾琳也没有放过。重点当然是陶文贝,他们首先要弄清那一天的所有细节。她开始按原来设定的回应,即把金水换成了季府老爷: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要迎娶自己的人,遇到这种事当然怒不可遏。两天之后审问者告诉她:你的男人将被斩首。她吓昏了,改口说那个醉酒人不是别人杀死的,就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信这双纤手会夺下火铳和折断男人的颈骨,等于白说。由于事前安排周密,大家一口咬定顾先生等人早在两天前出院,并拿出一本登录为证。对方一时难寻破绽,又因为事涉洋人,巡防营和府衙就不再纠缠下去。
陶文贝开始定定地看我。经受这目光细致而长久的抚摸是至难之事,我觉得如同灼烤。“季老爷这为什么,我不明白……”我重复以前的话:“因为他侵犯了你,那就必得去死。这个人最好、也最应该被我杀死。”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命中注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你看,它来了。我说过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真可惜,可能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陶文贝刚刚止息的泪水又流下来。她转身时看到了地上的刑具,退开一步:“这是……”她蹲下细细地看,瘫在了那儿。我将她挽起时,觉得她的身体那么柔软轻盈,真的像一只小羊。她挣出我的手臂,泪水纵横。我没法安慰她。时光多么珍贵,可惜要被美人的泪水注满了。我轻轻说着,但能听出自己的嗓子发颤:“没什么,不过是这样罢了……让我们说点别的吧,说说你们医院,特别是雅西。对了,我觉得从第一次见他到现在,他一直不太喜欢我。”
最后一句让她怔了一下,泪水立刻不再流淌了。她的目光中有什么闪跳了一下。我的心跳变得快速而沉重。我一直盯住她的眼睛,直到这浓密的长睫垂下。“没有的季老爷,他们洋人就这样儿,蓝色的眼睛容易让人误解。他其实是一个极好的人。”我几乎要笑出来。多么美妙的修辞,除非是她才能想得出。我爱她容颜与聪慧互为表里的极致。同时我却想到了伊普特,同样是一副蓝眼睛,在他那儿却让我感到了慈父般的温良。我不再说什么。
“我不相信会这样,就是不相信!”陶文贝一低头又看到了那副刑具,叫着。她在极度绝望的时候差一点要扑到我的怀中,但总也没有。我渴望在这意味着诀别的时刻紧紧相拥,抚摸她一头滑爽的黑发。没有,真实的情形是,她并非我的女人,她只是西医院的一个医助,是不小心卷到命案中的女子。季府对麒麟医院有了亏欠,最亏欠的还是面前这个人。
这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面色激烈而果决的兄长徐竞,他行前曾对我发出命令:向这个可爱的女子发起致命的进攻。是的,我在内心里早已接受了兄长的指令,不幸的是整场战役即将结束,自己已弹尽粮绝。我看着她,摇头:“我是一个失败者。”
“别这样说!我们所有人,伊普特院长和雅西,正联合教会的人一起救你!一封求诉书早就递到了府衙……你千万要挺住啊,你不能这么灰心丧气!”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我和你。”
陶文贝再次仰起晶莹的泪眼。她不知是否听懂了,只是摇头,呼吸越来越急促。她像害冷一样双手抱住了胸部,牙齿磕打出声音。她说:
“我求求你挺住,你不能灰心,因为还没到最后……还有,你不是一直在等我的回信吗?你还没有收到我的回信!”
8
大概就为了留下一个诱人的悬念,她直到离开都没有透露回信的一丝内容。多么傻的姑娘,如果仅仅如此就能挽救我的生命,该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啊。我再次认定这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孩子,同时也为她的倔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事情的结局极可能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她的那封回信将再也找不到地方投递,留下永生的遗憾。
我含泪远望她离去的背影,直到空空的远方。我不须猜想她的回信,那只会换来更多的痛苦。我将余下的不多时间用来想念兄长吧,因为一切都是因他而生。如果我的导师所言不虚,他和父亲的分手真的是那个原因,那么这其中兄长必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是一个令我钦敬和惧怕交织一起的人,一个无论如何都要挂念和依赖的人。说实话,我对他和他的朋友所做的一切躲避唯恐不及,可奇怪的是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去做他们指派的任何一件事。这已成为季府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从父亲开始就是这样了。
这大约是一种宿命:半岛上首屈一指的豪富、独药师传人,必定要和革命党人连在一起。
我等待一个恐怖的时刻。这大概不远了。
那个时刻的到来将有一个响亮的信号,它是由金属做成的某种声音,飘到树梢上微微停留,再像蝉鸣一样颤抖着滑到地面,毫不留情和确凿无疑地落在我的门口。这扇黑门不久就会打开,然后走出一个披枷戴锁的人。
每天半上午时分,这样的信号都有可能到来,我张开敏锐的触角和听觉,准备接收。那位爵爷送我的宝贵之极的礼物,即用所谓价值千金的秘传独方换来的上等马桶,已经三天多未能派上大的用场了,原因是本人胃口全无。奇怪的是第四天上午,我竟然不得不坐在爵爷的奇物上,仿佛要最后消受一下。也就在这个当口,那个金属般的信号响起来了:嘭嘭擂门,开锁,两个持刀兵士闯入,还跟了一个白脸文书模样的人。后者对坐在马桶上的我拱拳,说:“老爷,咱们走吧!”除了这几个字,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咬紧牙关将最后程序完成,一双手颤颤抖抖束起腰带。
门外阳光强烈,要用力忍住以防刺出满眼泪花。我的心一直狂跳,眼前发蒙,他们不得不上来搀住。我过了好久才稍稍镇定,手打眼罩看看前边,万分惊讶地发现了一顶轿子。这轿子足够豪华,轿夫衣着齐整。我转脸看那个白脸,他又一次躬腰礼让。我满腹狐疑地上了轿子。
坐稳后我鼓鼓勇气问:“请问这是……”他目视前方:“不远了,到了您就知道了。”我不再询问。帘子紧闭,我掀开一道缝,立刻被市相灼烫了一般:这一切久违了。来往不息的人群、挑担匆走的商贩,再分明不过地显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间。
街上的人流渐渐变疏了。街道变窄。两边出现了持刀背铳的人。我搓搓眼睛看了许久:没错,快了,前边就是府衙。真的,堂皇的大门到了,轿子一停,直接进到内里。这里有整齐的花树,有池塘和假山石。在一幢高大的楼宇跟前,我看到了表情肃穆的石狮。随引路人登上一层层石阶,最上面是几个穿官服的人。他们闪开一条路,让我们走入。正前方有一个老者,同样穿了官服,正朝我抱拳。好生熟悉。我缓缓抬头、仰视,这一刻蓦然认出:康永德。
9
一切宛如梦境,我需要用力走出一片迷茫,将自己唤醒。康永德衰老的容颜格外陌生,那增添了许多的老年斑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叹息,嗯嗯呀呀,好像并没有说出什么,这样一直与我走人厅堂。旁边的人待我们落座就退下了。四周洋溢着椒味儿,使人有一种庄严的感觉,这是大衙门才有的气息。
我彻底清醒过来,开始端量从未见过的道台府。我父亲与康永德交往时他还只是一个管带,所以可以断定父亲没有来过此地。这儿雕梁画栋,有点像庙宇,只是没有供奉塑佛而已。转脸看康大人,他笑眯眯的却不失威严,有点故扮神明的模样。我这才想起向他问安,拱手一拜。
“嗯,一别又是许久!老朽几次要去府上,无奈衙里事冗。我又该吃吃丹丸了,离开它终究不行……此事从长计议吧,季先生,你受了苦楚,这都怪老朽势单力薄啊,好不容易,唉,可谓一波三折……”
他眯眯眼睛看我,然后待我发问。我忍住了听下去。也许在接下去的瞬间,吉凶即可明了,这会儿还是免不了忐忑。场景移换太快,我无论如何都难以适应。不过自己面临的肯定不是一场审问,这种事不必烦劳大人亲自出面。我在最初的日子里不止一次求见面前这个人,全都失败了。但我内心深处或仍存一丝奢念:在最后的时光到来之前能与季府老友见上一面。也就在我完全不做期待的时候,这个人却终于露面了。奇怪的是我既没有大喜过望,也没有侥幸和乞求,只有绝望和等待。
“季先生想必知道,这个案子是巡抚、太子少保亲自办理的,惊动了朝廷,府衙是插不上手的。他们甚至不做通报。府上管家和仆人在这里跪泣,我事后才知。倒是见了洋人联署的折子,转呈后泥牛人海。这个案子太大了,太大了……”康永德胡须奓着,看看我,两手使劲按住椅子扶手。
我不动声色,一副听候发落的模样。
“老夫为季先生上奏三次,泣求,以性命做担保,言明道员无礼在先,而后才有这桩失手命案。其实我心如明镜,先生哪有这般生辣手段?杀人者绝非先生。不过……”
我听得分明,即刻打断他的话:“康大人开脱,在下心存感激。不过人的确为我所杀,一时怒发而已。”
“哈哈,不必说了。那道员是何等身手?他们可不是三两人能够近身的!你这双手能拧断他的脖子?以我看,你连一只兔子头都无可奈何!到底是谁所为,你我都知道,这会儿还是不说为好。”
我偏要问他:“是谁所为?”
“他们早就逃了。”
“案发两天前?这不可能啊!”
康永德将一口茶徐徐咽下,“当然是案发后了。我不明白的是季先生义气如此,自揽命案,要知道这可是天大的事啊!”
“那只脏爪碰了我的女人,也就成了我的事,与他人无关。堂堂季府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看护,会令世人嗤笑的!”
康永德全不在意我的慷慨大言,伸出胖胀的大手说:“罢了。我已对上申明,季老爷至多是交友不慎,罪不至死。我把府上百年盛事一一历数,尤其为半岛方士秘术之重镇、损折则独传秘方断绝无继详述周备,以身家性命许下保证,这才换来今天结局。季先生万万不可大意,世道凶险,乱党何等猖獗!从今以后要审慎过往,切不能轻许义气,冒杀身大祸啊……”
我句句听在心中,许久未语。我想听到他直指顾、金二人为乱党,但终究没有。这是一个权谋阴幽的上一代老人,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甚至想到:自己从关押的一刻至今,全部由他精心设计,其目的无非为了让季府主人彻底驯服,代价就是在锋利之刃上走一遭。冷汗从额头渗出。
“季先生,老夫今天为你压惊了,备下一席薄宴,酒足饭饱之后,我还要亲自送您回府。此事前后老朽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先生体谅。老朽一生得益于季府多多,算得上是过世老爷的门生,为季先生付出多少辛劳都是义不容辞……”
他这番话后,我也只有称谢。尽管满腹犹疑,难言的感激还是弥漫全身,一阵阵心跳强烈地撞着胸口。
“请吧季先生!”
“您请,康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