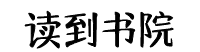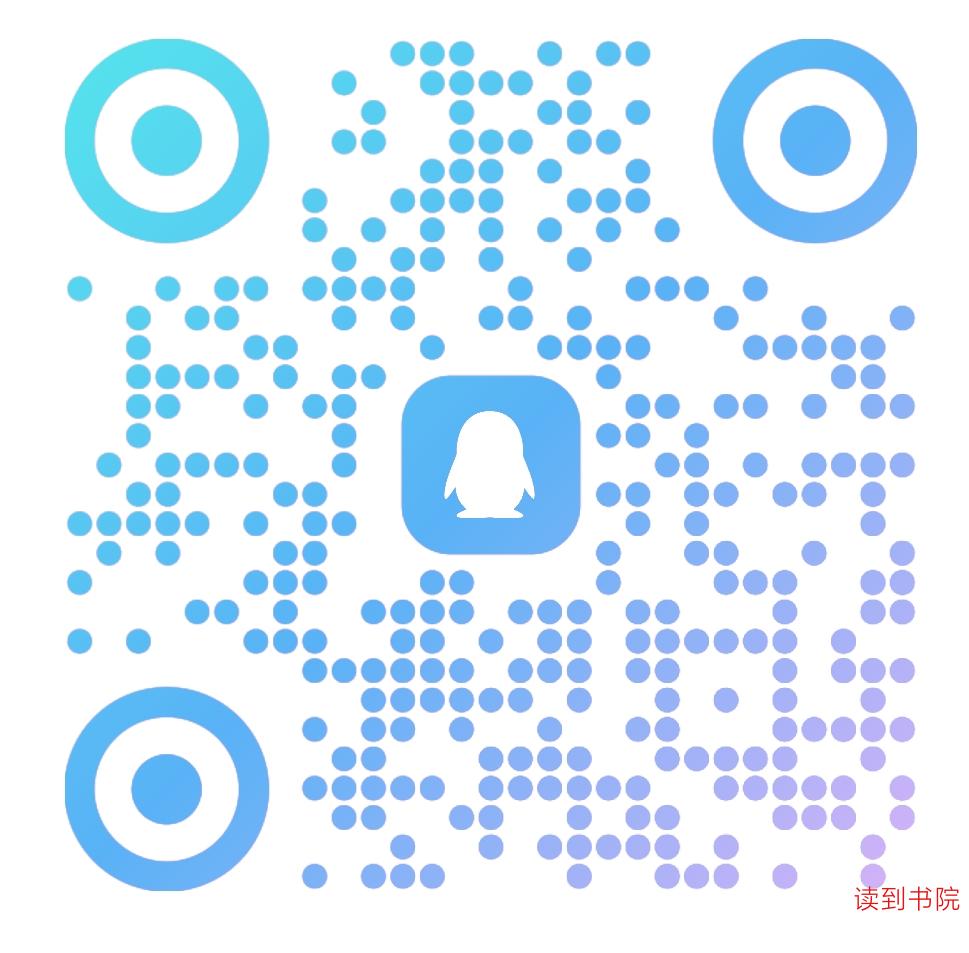天下着雨,秋风卷走白杨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有人在街上扯着嗓子唱歌,我们三个都扒着长沙发看向窗外。楼下,五次获得过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的罗多·卡莱姆正紧紧扶着栏杆。
“我亲爱的,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不管遇到熟人还是生人,我们的罗多总是没完没了地问这个问题,他像白狼一样因此出名。
他对别人有多殷勤,就对他的妻子和自己有多刻薄。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手脚并用,沿着通往戈里察高处的台阶往上爬。对于罗多来说,每天沿着戈鲁察路的陡坡一直走到顶,亲自征服每一级台阶,算是体育方面的成就,简直比得上在几场小型的奥运会上胜出了。
马上就要开冬奥会了,从此之后,在萨拉热窝,一切都以服务冬奥会为准则。即使这个冬天没下雪,而且都已经进入了一月份,人们还是很担心,目光中都是疑问。然而其他人却觉得举办奥运会纯属多余,他们从牙缝中挤出话来:
“呵……咱们真需要这玩意儿!”
只有老天才知道,为什么罗多竟然没听说奥运会的事儿。看到他突然踉跄了一下,我母亲吓坏了:
“瞧啊,他要摔倒了……”
话音刚落,罗多脚下一滑,摔得结结实实。他在摔倒时抓住了栏杆——它将街道分成了两级阶梯。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站起来,却没法以这个姿势支撑多久。他想找个台阶支撑一下,没想到一脚踩空了;他再次拽住栏杆,用脑袋抵着站起身来,结果又摔倒了。一看到血,我母亲紧张得咬住自己的手。父亲急匆匆跑到过道里,没穿鞋子就冲出了家门。
“我的天呐,布拉措!你不能光着脚跑到街上去啊。”
“我没光着脚,穿着袜子呢。”
我母亲跟在我父亲身后冲了出去,手里拿着他的皮鞋。
他们把盯着天空看的罗多扶了起来。
“你没死吧,罗多?”我在他旁边大叫。
他嘴里嘟哝着不知什么,那双亚得里亚海一样蓝的眼睛在看什么,也只有天晓得。
“他一定是从喀尔巴阡山那边来的,”我对父亲说,“跟所有的斯拉夫人一个样!”
“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他去年就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母亲插嘴道。
“阿兹拉,别对孩子乱说!”
“我没乱说啊,他之前在杜塞尔多夫他哥哥那儿,在一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星期的活儿。”
“嗯……他喝醉啦!”我做了总结,母亲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头一放在枕头上,罗多立刻认出了我:
“呀……瞧瞧他!一个卡莱姆,真真儿的!蓝眼珠,这是天之悲伤。”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即便我并不是太想知道答案。不过,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不一会儿,我就带着“蓝眼珠是天之悲伤”的感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正守在窗边,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罗多在我家厨房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他一大早就醒了,然后照着住公寓的习惯忙活起来。他这么做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喜欢帮别人一把,也因此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父亲一睁眼就看到了那台被罗多拆得七零八落的收音机,零件散得到处都是。
“我什么都能想象,不过,一个人类的声音能够漂洋过海传进我的耳朵里,这可真是奇迹!”罗多感叹道。
“也许是靠上天呢?”
“上天传递信号。”
“意思是老天也知道啦?”我父亲问。
“一点儿没错!”罗多说。
他堵住厨房盥洗池的下水口,往池中放了些水,然后让水滴不断地从水龙头滴下来。
与此同时,我父亲和母亲都俯身凑到跟前,观察水滴滴落的周围,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波纹。
“就是这个原理,我亲爱的们!”
“可是……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扩散的水波。”
“老天还会点儿小儿科的东西呀!”
“别再说你的老天了,信号就像一滴水,老天让它落在大海里!这就是全部的奥秘!”
通过厨房半掩着的门,可以看到录音机的几千个零件,餐桌上、橱柜上、长沙发上,还有两把扶手椅上,都铺满了!凭着魔术师般的灵巧,罗多很快就把它们重新安装好了。他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我们马上就听到了新闻:“……今天,铁托同志在访问斯梅代雷沃(1)时再次强调,革命和日常生活是两码事!……”
“必须从厂子里再拿个新的电容器来。这得花些时间了……”罗多解释道。
“啊,好的!你能不能也看看电风扇,”我母亲说,“它总是吱嘎吱嘎地响……”
“没问题,亲爱的。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说。”
电风扇一修好,我母亲又很快发现了别的问题。
“电视……二台不太清楚……”
罗多把电视机捣鼓了一番,很快就找出了故障:
“是地线,不算什么事儿!”
他抓起缆线——当他拿着的时候,电视画面很清楚;可等他一松开手,电视就嗡嗡作响,画面也走了样。他走到门口,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又说了一遍:
“只要有需要,你们就给我打电话!”
“好的。不过,下一次,拜托正正常常地来吧!”
“替我向天之悲伤的蓝眼珠问好!”
罗多走了以后,我一晃一晃地走到厨房,像往常一样,母亲再次重申她不喜欢我走路的方式:
“别拖着脚走路,站直了!”
萨拉热窝奥林匹克运动会越来越近了。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只不过,还是没有下雪。所有人对此都表示讶异:元旦都过了,可是雪呢……一点儿没下!
我最喜欢的日子是周一——因为这一天,我直到下午才有课。那天早上我睡了很久,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一醒过来,我点上一支父亲的黑塞哥维那香烟,又给自己弄了点儿咖啡。我在窗子前天马行空地想了好久。
风很冷,街上空无一人。我刚刚朝街上瞥了一眼,发现罗多出现在一棵白杨树下,醉得一塌糊涂——而且很可能,从头天晚上就醉了。他在风中摇摇晃晃,唱着,跳着,两只脚磕磕绊绊。我赶紧下楼去迎,还用上了游击队救伤员的技巧,还挺有效的。我迅速把他的胳膊架在我的脖子上,拖着他朝家里走。
到了家门口,他自己站直了身子,或多或少清醒了些,准备要走。
“亲爱的……我走啦……不过要是有需要……”他含糊不清地说着,瘫倒在地。
我没了力气,实在没办法把罗多拖进家里,幸好他似乎睡着了——我如释重负,因为我上学已经要迟到了。
我急切地盼望着最后一节课赶快结束,心情就像鲍勃·比蒙(2)脚踏起跑器等待着发令枪响。我回到家时,看到罗多还在楼道里。我母亲已经回来了,不过她没能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他拖到屋子里。
两个人,也就轻松多了:我抓住罗多的肩,母亲抓住他的脚,罗多终于在厨房的长沙发上“成功着陆”了。
“之前我每隔五分钟就得确认一下他是否还活着!得了,我叫急诊。”
“等等,让我试试!”
我捏住罗多的鼻子,他开始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用再叫急诊了:他还活着!
父亲回来了,从记者招待会上回来的他,显得有点激动。
“罗多回来了吗?”
“他在那儿呢。睡觉呢。”
父亲去把罗多叫醒。然后,他阴沉着脸回到桌边吃饭,顺带叫罗多马上来。
“你们知道吗,刚刚曝出一件丑闻,”他在吃两口饭的间隙向我们宣布,“还是国际性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母亲问道。
“你,你坐在那儿!”父亲命令罗多。
“好的,我亲爱的,发生什么事情了?”罗多重复道。
“萨拉热窝要举办冬奥会,你知道吧?”
“就连树枝上的鸟都听说了!”
“可你知道吗?萨拉热窝都没有空床位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亲爱的?”罗多回答说。
“一个男孩让人收拾了……捷克的报社记者。”
父亲说的是什么,我们一点儿都没听懂。
“罗多,你怎么知道他到处勾引女人?”
“呃,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我亲爱的。我又不是瞎子!”
“那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在我家干什么呢?!’我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跟我说了几句外国话,我上去就给他一拳!结果我那好老婆倒朝我扑过来了。‘快住手!’她对我说,‘我跟你解释!’‘畜生!该是我向你解释吧!’‘误会……’那个家伙说。‘误会……你听!’‘他是个记者!’她说。‘记者……那咱们走着瞧!……’说着,我又给了那家伙一拳。他没有躲闪。他们这种人,撒谎就跟呼吸一样平常!他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了……我老婆,我把她锁在浴室了!另外那个家伙好像失去知觉了。我把他的脑袋摁到水龙头底下,他又清醒过来一点儿。我就把他送到了急诊室!即使我没送,他也没事儿,他什么都不会说,另外,也没人会再说他了。”
“你真是疯了!”
“啊?”
“你想想啊,罗多,送去急诊,他们会通知警察,告诉警察他是在哪儿被打的。警察肯定已经在追你了,我的天呐!你老婆跟他们说,她把一间卧室租给了这个外国人,她打算用赚来的房租给厨房换块油毡布呢!”
“可你啊,”我母亲微笑着插嘴道,“你把那个像初生婴儿一般无辜的家伙一顿胖揍,就因为你以为他专门勾搭女人!”
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
“阿兹拉,这可不好笑!”
“噢!怎么会啊,这太好笑了!一个为了奥运会而来的家伙,安安静静租个卧室……然后,就被——打——啦——!”
“这是一场误会!”
“所以才好笑啊!”
“要是他因为这个被关进去两年,你还觉得好笑吗?”父亲反驳道。
“不要!”我有些哽咽,“这不是他的错!要是你一回家,就看到一个家伙正在用你的牙签,你会怎么想啊?!”
我跑出门,坐在楼梯上,开始哭起来。
伴随着父亲和罗多的谈话,飘起了片片雪花——奥运会开幕式前夜,它们终于纷纷扬扬飘落向人间。萧瑟的北风没能吹弯白杨的枝条,于是它大发雷霆。晾衣绳上的滑轮吱嘎作响,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全都是因为我放心不下罗多,唯恐他真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被警察抓了去,无论如何,我想我的世界会崩溃的。就在这时,军医院那边出现了一辆小蓝车,是一辆警车!我顾不上哭了,飞快地跑回家里。还是有时间把罗多藏到地下室的。
父亲用两只手支着脑袋。
“那……”母亲问道,“咱们该怎么办?”
“要是我们把他藏起来……”
“没门儿!”
“为什么呀?”
“窝藏罪犯是犯法的。”
好吧……我心想。该轮到我表演了。
“最好的办法,”我提议,“就是让他去向警察自首。趁着警察还没来!”
“照你看,我亲爱的,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减刑啊?”罗多问道。
“对!必须的!”
“天之悲伤的蓝眼珠,瞧我干了多蠢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学我。”
老天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计上心来:
“我陪你到警察局去!”我一边说,一边戒备地留意着窗外,生怕警灯出现。
“哇!太棒了!我儿子的分析能力……”父亲不胜欣喜,感叹道。
“我准备好了,你们不会怨我吧,嗯?嘿,天空的眼睛,咱们出发!”
我们下了楼梯,走到了进门处的大厅。正当罗多打算出门时,我一把扯住了他的袖子:
“别从那儿走!有警察!”
罗多一脸茫然,紧跟着我一路小跑直到地下室。我摘下扣锁,让他进去。
“你不该这么做,我亲爱的。”
我刚关上门,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穿便衣的,他们按响了我家的门铃。我把家里装卷心菜的桶盖掀开,搬出几个卷心菜放到了邻居加夫里奇的桶里,因为他的桶有一半还空着。罗多跳到桶里,我把盖子盖好,离开了地下室。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会对警察说些什么,不过第三个警察,就是穿便衣的那个,去四周搜查了。
“真丢人啊!一个咱们这样的民族,连世界另一头的人都在赞扬我们热情好客!”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你们想拿他怎样呢,他不是个坏人……”
“不是坏人?!要是我们把别人痛打一顿,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呢?”
“这个啊,我也跟他说过了。”
这几个警察拿着手电筒在大厅里扫了好一会,接着就下楼去地下室了。我躲在阁楼,把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我蹲坐在脚后跟上,守在阁楼门口。看到他们从地下室里上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跟你们说过了,他去自首了,”我父亲解释道,“警察局的人怎么会没通知你们呢,真奇怪。”
我又在阁楼藏了半个小时,才下楼回到家里。
“还顺利吗?他去警察局自首了?”父亲问。
“我一直把他送到苏捷斯卡电影院那里。他朝我做了个手势,跟我说:‘向你爸妈问好,我亲爱的!’”
“他这么了结还算聪明!”
“是啊,对,说得没错!”
这个夜晚很平静,可是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去睡觉。而我,我还在等他们睡觉了,再下去给罗多送吃的。父亲还在看电视,而母亲正在给我织新毛衣。
“阿兹拉,我更喜欢细毛衣!”
“我可没钱买……”
她继续手头的活儿。
我用尽浑身解数想让他们快点儿走,这样才能让罗多吃上饭。可惜都是白费力气。
罗多肯定生气了,我心想。于是我大声提议:
“酸醋汁卷心菜……哎,我真想来点儿。”
“都这个时辰了,我才不会去地下室,我的小宝贝!”
“你不用管了,”父亲说着站起身来,“我去。”
“别……不用啦。我好像有点胃疼……”
“那就别吃卷心菜了,也别吃维生素C了。量量体温,你快去床上躺着吧。”
我立刻爬上床,钻到鸭绒被底下,迫不及待地等着父母去睡觉。可在此之前我先睡着了。
早上五点钟我就醒了,心想罗多肯定饿死了。母亲睁开眼,看起来有些担心。
“你去哪儿?”
“去厕所。我肚子疼。”
我跑到厨房,像电影里的快进镜头一样,从冰箱里摸到什么就往外拿。然后我偷偷溜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看看家里没什么动静,赶紧打开地下室的扣锁。我用手电筒照着,慢慢走到卷心菜桶旁边。我把手电筒放在通风窗的窗台上,然后掀开盖子。
“罗多,是我。你听见了吗?”
没有回答。我顿时慌了神儿。我把里头的卷心菜一个接一个往外搬,不过很快我就明白过来,罗多已经逃走了。藏人的主意原本让我沾沾自喜,可没想到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
“阿列克萨,你在哪儿啊?”
“在这儿呢。”
“你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我想透透气来着,我肚子疼。”那个夜晚,不仅仅是一个笼罩大地的黑暗之夜,更是我初次违法乱纪之夜。我本想跨过红线,却没能成功。我只好重新回到床上。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我父亲叫我起床,我求他再让我多睡五分钟。我闭上眼睛。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
“……昨天晚上,就在萨拉热窝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前夜,有人以非正式的方式为滑雪道举行了开幕式典礼。两位成年男子,家住萨拉热窝戈里察街区的米连·罗多·卡莱姆,以及滑雪道守卫、帕莱(3)本地人德扬·米特洛维奇无端指责,雪橇在滑雪道上下滑的速度太慢。于是两人决定打赌:只要有一瓶拉吉拉,罗多就脚踩塑料袋顺着滑雪道冲下去。赌注一下,两人……说干就干。”
一群赌徒发现罗多时,他的皮肤都烧焦了,他们把半死不活的他送进了医院。打这之后,不论是父亲还是萨拉热窝警察局,都不再操心这位技术员——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罗多曾经制造的那个丑闻了。
当我们到市医院去探望罗多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缠着绷带,一动不动。他看着我们,费力地问我:
“我庆爱的,你们有什么洗要吗?”(4)
(1) 南斯拉夫东部城市。
(2) 鲍勃·比蒙(Bob Beamon,1946— ),美国田径运动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跳远项目世界冠军。——编者注
(3) 坐落于萨拉热窝东南的市镇。
(4) 在原文中,罗多因为受伤说话吐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