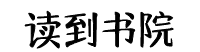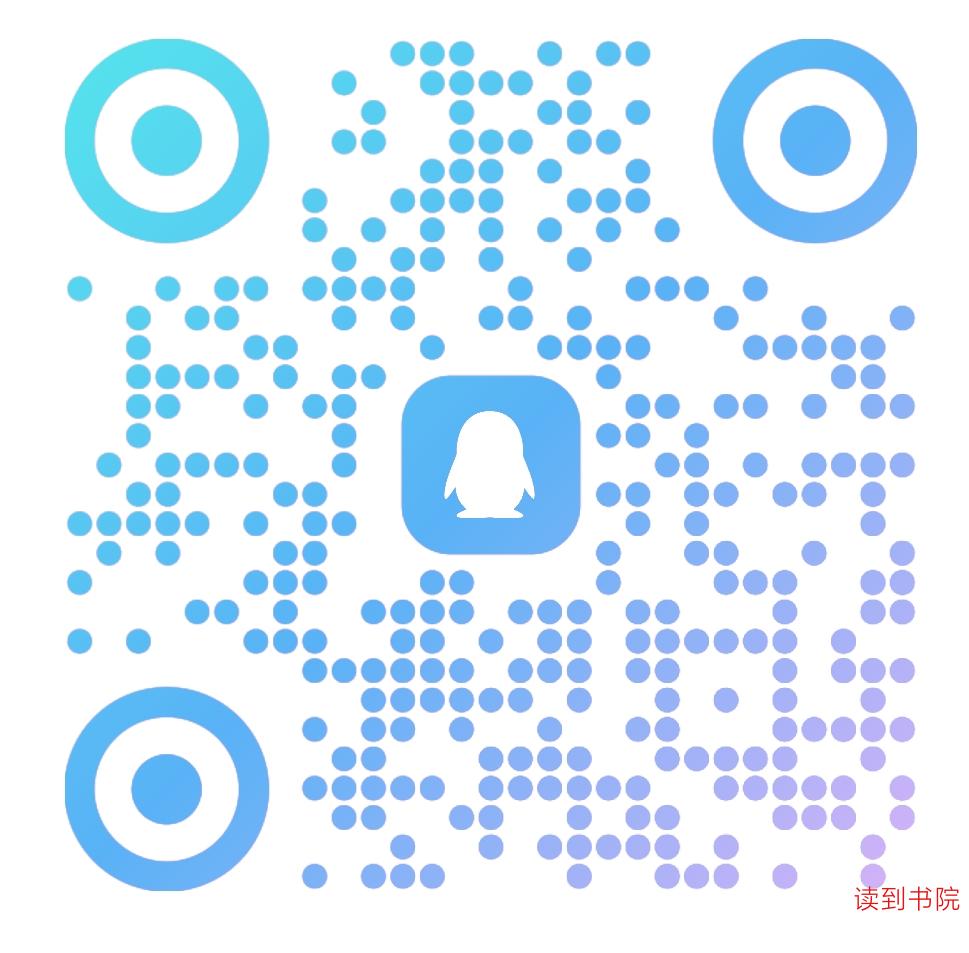我收到一本布兰科·乔皮奇写的《驴子的岁月》,是从贝尔格莱德寄来的。一封信从包裹里掉出来,上面盖着萨拉热窝中央邮局的印戳,还写着地址:阿夫多·亚布奇卡路22号,阿列克萨·卡莱姆收。这是我以自己的名义收到的第一个包裹。在明信片的背面,国际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安娜·卡莱姆写道:致我亲爱的阿列克萨。十周岁生日快乐!姑妈安娜。
这个礼物并不让我开心。我一大早就忧心忡忡地去了学校。大课间的下课铃声响了,我第一个跑去“大人们的”厕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家在那里吸烟。学校里都抽LD过滤嘴卷烟,因为可以单支购买。只要一支就够3C班十个学生抽了。
“不是这样!”科罗指责茨尔尼,“你得长长地往里吸一口,让烟气一直到达脚指头。”
他好像在解释该怎么吸烟,可实际上,他是想趁此机会在轮到自己之前多吸几口。
“我有个该死的问题……”我突然袒露心声,“我该怎么办呢?”
“这得看情况……是关于什么的?”
“他们想强迫我看书,我宁愿去少管所。”
“我有个法子。”
我差点呛到自己;这可是黑塞哥维那烟啊!即使是大课间,我们也没办法一直抽下去。
“法子?什么法子?”
“从现在起直到今年年底,我哥哥得读完巴尔扎克的《红与黑》。”
“是司汤达的。巴尔扎克写的是《高老头》!”
“可是你让我帮忙的,你怎么这么烦人!”
“我敢打包票啊……”
“知道谁写的什么,这很重要吗?好啦,你好好听着……在学校里,他们对我哥哥说,要是他不看那本该死的书,就让他重读七年级。我妈妈让他乖乖坐在椅子上,威胁他说:‘我会一直监督你,直到你读完这本书!就算你看得想吐了,我也会一直盯着你,但那个该死的家伙,你也必须要读完他的书!’”
“哪个家伙?”
“嗯……巴尔扎克,记住了吧!听完这些话,米拉莱姆就开始唉声叹气:‘可是妈妈,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啊?’我妈妈立刻把他的话顶了回去:‘你还敢问我?!你那可怜的爸爸当了一辈子搬运工。可是你呢,你绝对不能和他一样!要不然,还有什么希望啊!’然后,她就把米拉莱姆捆上了。本来就该如此!”
“接着说啊,用什么捆的?”
“熨斗的电线。然后她打发我去图书馆找那本书。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米拉莱姆给我使了个眼色,又往我手里塞了个纸条:‘你去肉店老板拉希姆那里。让他给我切一百五十片薄薄的牛肉干。’我去了图书馆,然后去了肉店;拉希姆把肉切成了可以嚼的小薄片,每两页之间夹一片。晚上,我妈妈坐在米拉莱姆对面的长沙发上,她准备了满满一壶咖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哥哥。而我哥哥呢,他表面上在看书,实际上是在贪婪地盯着牛肉干,等他想吃的时候,就假装为了翻页把书快速地往后翻,然后趁机把一片肉吞进嘴里。这一百五十片牛肉干让他翻了三百页书。我妈妈还以为他把书都看完了!”
就因为《驴子的岁月》,我们家有点一反常态。我父母不去操心重要的事,反而开始关注我有没有读过哪些世界文学名著,并列了一份清单。
“告诉我,妈妈,如果不读书,人会死吗?”
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她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并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突然想到,她可能和科罗的妈妈串通好了,而且也学了人家捆绑的招儿。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可绝对没办法模仿米拉莱姆……我特别讨厌牛肉干!只要一想到油腻腻的东西,我的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可我母亲使用的是战略:
“你看这书多灵巧啊,”她边说边用手抚摸着几本精装书的封皮,“只要读一本,你就能学到一个新词。这个规律,你应该听说过吧?”
丰富我的词汇量,对此我无动于衷。她向我展示卡尔·麦(1)的《亡命小道》、佩罗·科伍尔茨卡的《社会》、马托·罗夫拉克(2)的《雪中列车》。所有这些鼓励我读书的行为都让我心烦意乱。我没办法平息下来。布兰科·乔皮奇是姑妈的一位老相识,这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她认识的不是阿西莫·费尔哈托维奇(3)呢?他兴许可以让我免费去看萨拉热窝FK的比赛呢!”
“你姑妈是一位革命者,阿列克萨!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千万不能显得你很肤浅!”
“什么?你竟然觉得哈斯(4)肤浅!”
我胡搅蛮缠起来。这可是曾经单枪匹马靠3比1的成绩战胜了迪纳摩萨格勒布(5)的足球运动员啊!要是有人侮辱他,我会发怒的。
“我可没针对你的费尔哈托维奇,我的儿子,但你的祖父和外公都是公务员,你可不能跟书本作对呀!”
“得了吧,我也没被强迫去踢足球呢!那部电影,你们才不会去看呢!”
仿佛林火被风吹得越来越旺,我的怒气也越来越盛。就在这时,我母亲拿起了熨斗。
“啊,不!”我叫嚷着,“你总不至于用电线捆我吧?!”
“谁说要捆你了?”我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是失去理智了吗?”
心理上的压力没有产生任何作用,除了体育赛事报告,我根本就不想看别的。为了表示抗议,我甚至关注起了《新闻晚报》中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版面的内容。床头柜上堆着我第一批该看的书。我父亲现在相信:我是成不了知识分子的。
“如果他非要这么固执,咱们也没办法。让他玩吧,毕竟他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也许有一天,他自己就开窍了!”
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这话。母亲刚帮我把盖在身上的羊绒被塞好,我就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里:一个偌大的盥洗池出现在我面前,就像巴什察尔希亚(6)的土耳其浴池那么大!里面还有一块洗碗布。远远地,我看见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需要疏通盥洗池。水从龙头里不停往外流,都已经溢出来了,开始灌满我的脑袋。我醒着,意识非常清醒,但双手却怎么也动不了。最后,大半夜里我尖叫着醒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邻居兹维狄克会这么说的。
“怎么了,我的小心肝?”母亲问我,“你的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厉害?”
我该怎么跟她说,父亲的话对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求你了,告诉布拉措别再烦我了!”我呜咽着。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安慰着我。
“可是,阿列克萨,他只是希望你好啊!”
突然,我明白了“通往地狱的路,往往由善意铺成”的含义。但愿布拉措不会有那么多善意。
“你看见了吗?”
她用手指指着我的肚脐。
“嗯。然后呢?”
“这是你的灵魂之门。”
“肚脐……灵魂之门?你别说笑了!”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书籍正是灵魂的食粮。”
“那我不需要灵魂。”
“人活着,就不能没有灵魂。”
“那……灵魂……能吃吗?”
“不能。但是为了不让它枯萎,就要读书。”
她在我身上抓痒痒,我挤出一丝微笑;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轻易相信了她那关于灵魂的说辞。
“我还不是个男人呢。”
“怎么?”
“只有长大了,才会成为男人啊!”
我根本不想对母亲发脾气,可能是因为我确信自己做得没错。可她对我说的那些大话让我心烦意乱。
阿兹拉一直在摸索如何才能把我引向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她想起我是南斯拉夫童子军团的成员。于是,一天晚上,她把斯特万·布拉伊奇(7)的《水獭湖童子军》带到了我的房间。
“喏,读读这个。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的儿子!”
“阿兹拉,我求你了。现在就惩罚我吧。你还不如让我跪在大米粒儿上呢!你和我,咱们两个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为什么要惩罚你啊?你又没做坏事!”
“因为你们的文学啊,真是酷刑!只要看到第三页,我两眼就开始乱瞟了,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宁肯跪大米粒儿,也不要看你们的那些书!”
童子军的招数宣布告吹,我母亲决定选择更加通俗的文学:知道比起西部牛仔我更喜欢印第安人,她用自己的年终奖买了卡尔·麦的全套图书。亲爱的印第安人并不比之前的主人公们成功多少。每次都一样,看到第三页我的眼睛就开始乱瞟,到第四页目光呆滞,到第五页的时候大脑都僵住了。
等到最后一丝耐心都被耗尽,我父亲泰然自若地悟出一个道理:从此以后,不用指望卡莱姆家再出知识分子了。
“儿子,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你最后就会像苏联的小说主人公奥勃洛莫夫(8)一样:等到退休的时候才读你的第一本书!”父亲喝着他的咖啡下定结论,萨拉热窝电台上正在播放每日流行歌曲。
我正准备去上学。在上班之前,他对我下了定论:
“得了……就这样了,不可能有其他可能了!”
“这个奥勃洛莫夫,是谁啊?”我问我母亲,“那个人就不能不用他那些苏联革命者来烦我吗?我跟这些冒险家没有一点瓜葛!”
“好吧,不是‘那个人’,是你爸爸。奥勃洛莫夫……我不知道他!”
“阿兹拉,你们的文学,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你站到戈里察的高处看看,那才是文学!每一天,它就发生在我眼前。在那儿,茨冈人每天都在创造真正的小说、真正的故事——最后,就成了你们所谓的历史。”
“读书就是为了比较自己与他人的生活,说到底,是为了长大!”
“如果我不想长大呢?”
“那不可能。”
“既然我能够在真实的生活中阅读,为什么还要看用文字写的书呢?你告诉我啊!”
“人的大脑需要训练,因为它就是一小块肌肉,你知道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更好的办法。”
“比阅读还好?你说说看,我听着……”
“在沟槽里滚小球,锻炼这一小块肌肉啊!”
“胡说八道!”
“啊呀,现在是夏天,夏天还读书,你们怎么想出来的?”
“我的小儿子呀,我觉得你是在嘲笑我们,而且你偷着读书了。”
“怎么?”
“看你自我表达的方式。你至少已经读过三本书了!”
为了去度假,我们得从诺尔马勒那车站坐车到马卡尔斯卡。一上大客车,阿兹拉就先给我贴了片晕车贴,然后她自己也吃了一片晕车药。等到了哈继奇,我就已经开始吐得死去活来。车走到科尼茨,悲剧发生了:司机拒绝停车。
“得了吧!除非遇到什么严重的突发事故,否则我是不能停车的!我得走固定的路线!”
“你就不害臊吗!这孩子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而你呢,你还跟我说什么路线!路线对他又算什么呢?”
“就是要沿着线路走,蠢女人!”有人像熊一般吼了一句。
“真是倔骡子脑袋!要是我停车了,他们会扣我工资的!那我的孩子呢,难道你来养他们吗?”
“你要是不停车,我就勒死你!去你他妈的路线!”
我母亲站在司机背后,两只手紧紧攥着的,是用来勒死他的毛巾。
司机见状,立刻把车停在路边。我一个箭步冲到车外,精疲力竭,大吐特吐。我弓着背,就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白杨树。我看到车上的乘客们压得车身向一侧倾斜,他们都在看我。头顶上,是一轮大得出奇的圆月。
“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啊,同志。”
“你确定没什么更严重的了吗?”一位老妇人关切地问道。
“没事,”我母亲说,“这孩子一坐车就不舒服。”
过了梅特科维奇,困意向我袭来。就好像之前我没有吐过一样。睡觉可以让我很快得到休息,但与此同时,一个主意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在我与阅读的战斗中,疲劳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收拾行李的时候,阿兹拉偷偷往其中一个包里塞了本《大卫·克洛科特(9)传》,还是插图本。在车上的时候,她就已经拿出书来随手翻看,还时不时把书合上,为的是展示书的封皮——她希望能够用封皮上的金发小孩来吸引我的注意,他头戴一顶动物皮毛做的无边圆帽,帽子后面还有一条尾巴垂下来,搭在他的肩上,就像克拉斯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印着的几个扎发辫的姑娘,辫子垂到她们的胸口。
天亮时,大巴在一股腐烂水果的气味中停靠在了马卡尔斯卡,因为长途汽车站紧邻着市场。摆满了梅特科维奇特色商品的货摊上,坐着一个结实的大个子,嘴里唱着“和斯普利特比起来,伦敦又有什么好,噢,时髦的女人”。
“周末过得好吧?”他问一个正在码放辣椒的男人。
“周末?糟糕透了!打雷下雨,都快赶上迪纳摩了!”
在一幢散发着霉味的双层别墅的院子里,一个鸡蛋头、浓眉、红脸的家伙正拿着钥匙等我们,他是这里的房主。只见他脸上的毛细血管都充了血。
“老天保佑!别让我们撞见酒鬼、闻到烈酒了!”我母亲低声说道。
“不是烈酒,阿兹拉!他喝的是葡萄酒。”我说。
“都一样,还不都是酒精嘛!”
我能够分辨两者,还要归功于父母的卧室——父亲头一天晚上喝了不同的酒,墙壁就会散发不同的味道。
“那个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我们才刚到,他不说拿无花果招待小孩子,反倒问我为什么没给他寄钱!更可气的是,他竟然还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来了!’”
房间里出现了新的不快。阿兹拉毫不客气地指责起来:
“这是浴巾吗?啊?还不如一块洗碗布!”
说罢,她把那几条毛巾丢到地上,从一个包里拿出我们自己的毛巾、被单和毯子,用我们从萨拉热窝带过来的床单重新铺好床:
“好啦!现在,假期可以开始啦……”
“就好像她要举办奥运会开幕式似的。”被睡意征服前,我心里这样想。
如果说房间里弥漫着的腐烂气味和从地下室里冒出来的酒酸味,让这栋房子更加一无是处,它至少能让我逃离世界文学。这房子离海滩两公里远,长途跋涉带来的疲惫也十分有帮助。
然而,母亲并没有放弃强迫我读书。她不停地拿着那本《大卫·克洛科特传》在我眼前晃动。就在她读书的时候,我看见她强作笑颜。我才不上钩呢。在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半路,我就决定给阅读再加一记猛拳:
“阿兹拉,你背着我。我站不住了……”
让一位母亲背着一个九岁大的儿子,而且还跟她差不多高,好吧,这是不太正常,不过我们离住的地方已经不太远了;那天晚上,我的计划奏效了!我得为第二天再想一个新计划。
几个年纪与我相仿的男孩子正在港口打水球——他们是当地水球俱乐部的。
“我妈妈也想让我锻炼,”我对他们说道,“可是在萨拉热窝根本没有条件,要是换作你,你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套用了父亲提出要求的方式,只不过把他的话转化成了我自己的语言。因为在他空闲的时候,他会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谈政治,巴尔干人对公共设施没有任何概念,他对此尤为关注。当然,他还打出了王牌:那就是我们城里没有游泳池的事实。尽管有时候也会听说,帕夫莱·卢卡茨和米尔科·彼得尼奇在班巴萨练习水球……
我成功地说服了我母亲,她决定去马卡尔斯卡的俱乐部见见教练。
“为什么不呢?”教练一边测量我的身高一边说道,“他要是长大了,肯定有韦力·约热那么高!”
“也就是说你在身高和体型方面,是个典型的第纳尔人啦!”母亲自豪地对我宣布。从我小时候开始,她就给我喂各种水果、蔬菜以及恶臭无比的鱼肝油。
游泳和传球都不简单,更不用提射中球门了。在水下——我的脑袋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我回想起莫拉登·德里塞(10)毫不吝惜地鼓励我们这些新手的话:“我们的后继者们以5比1的成绩战胜了匈牙利队!祝贺杨科维奇!感谢他的父亲,感谢他的母亲!”
晚上,我勉强有力气啃完一大块面包,精疲力竭瘫在沙发上,只得靠母亲帮我脱衣服、抱我上床睡觉了。直到我们在马卡尔斯卡的最后一天,谁都没有再提起读书的事儿。
最后那天,等到太阳都藏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法把视线从大海移开。我连游泳的事都无暇顾及,一想到接下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再也看不到浮现在水中的巨大的圆形礁石,我就觉得悲伤。我注视着涟漪碰触到海滩上的卵石溅起水花朵朵,我试着想象空无一人的海滩。当滂沱大雨倾泻而下时,我不在那里;当狂风卷携断枝残叶时,我也看不到;当一团团荆棘在海滩上翻滚时,我也无法追逐它们——所有这一切让我忧伤不已。尤其是,我再也看不到这里光芒四射的太阳了!
正是这种痛苦,引起了肚脐下的阵阵剧痛,所以俄语里把肚子叫作?ivot(11),这是父亲有一天告诉我的。
我弯下腰,喝了一口海水,来强化关于这个假期的回忆。
小道格拉斯从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我两只耳朵里生疼。当压力转移到了眼睛上时,我真担心它们从眼眶里迸出来。
“要是没有眼睛,我就再也不用被迫读书了!”我小声嘟囔着,生怕被阿兹拉听见。
这种可能性并未使我感到不快。当我们在苏尔钦(12)降落时,我的耳朵里突然一阵噼啪作响。天知道是为什么,但这是件好事。这也许又会成为一个对抗读书的好方法。
当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姑妈家时,我嘴中还有咸咸的味道。她的公寓离圣马尔科教堂很近,大门非常好辨认,因为那儿有一家叫作杜沙诺夫·格兰德的餐厅,他家的菜品远近闻名。姑妈住在特雷兹吉广场6号。我一口气冲到二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可当母亲按响门铃,一阵温柔的惶恐占据了我;每当见到与我非常亲的人,我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姑妈打开门,把我紧紧拥入怀中,非常幸福。很快,那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就在我身上苏醒过来了:
“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可真神气!”
“八月是这个城市最美的时候。”
“那些愁眉苦脸的贝尔格莱德人都到哪儿去了啊?”
“他们要么正在海里游泳,要么正在侍弄父母的花园。快跟我说说,你读完《驴子的岁月》了吗?”
我羞愧万分,急忙垂下眼帘。客厅里,肖邦、贝多芬、勇敢的战士帅克、莫扎特,都凝视着我。姑妈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去往世界各地,所以她时常带一些大人物的半身像回来。
“你为什么耷拉着脑袋呀?坦率点儿!你读没读过啊?”
“没有,姑妈。”我坦白地说道,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我又补充道:“你见过有谁在夏天看书的吗?”
她笑了。
“冷静点儿,阿列克萨。现在不是夏天了,早已经秋天啦。”
说罢,她径直走向书房,拿了一本书回来。
“喏。这本书,完全不用集中精力。”
她递给我埃米尔·库埃(13)的《自我暗示》,把书翻开,只见那页上写着:“每天看一眼,进步一点点。”
我大声朗读完这个句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不是真的吧!”
“所有的问题都在这儿。你喜欢这本书吗?”姑妈问道。
“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不可能……什么不可能?”
“呃,就是这个……每天看一点就能进步。”我冷笑着反驳道。
“那,你把这个句子给我重复一百遍。就算你觉得这不是真的,你最终也会相信的……”
于是那个下午,我母亲打电话给在萨拉热窝的我父亲。
“咱们儿子一直在重复‘每天看一眼,进步一点点’。而且,两只眼睛就没离开过手里那张白纸。他硬说自己是在集中精神!”
《驴子的岁月》成了我读的第一本书。通过这本书可以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我相信我也有一个。当我盯着空白点看时,书中的主人公,跟他的祖父一起来到了火车站,没有敲,就打开了我的灵魂之门。当他的祖父送他去寄宿学校时,小布兰科·乔皮奇穿过了这扇打开的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他还以为是一条蛇呢。这里便成了起点,当布兰科·乔皮奇笔下的所有主人公从这扇门鱼贯而入,就像为庆祝铁托诞辰的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的士兵。我突然明白了,我那关于夏天读书不合逻辑的理论是完全合理的。
我怎能忘记这个秋天和布兰科·乔皮奇带给我的欢乐?我又怎能忘记我父亲摆好姿势,与我们的大作家合影?照片是在欧罗巴酒店拍的,而那里正是我的父亲布拉措与布兰科·乔皮奇相识的地方。
布拉措听说他的儿子读完了第一本书,便招呼摄影师米奇·都拉斯克维奇前来酒店。母亲给我穿上节日盛装,搭有轨电车陪我赶到酒店。冰激凌很美味,正当我舔着第三个球时,父亲和布兰科·乔皮奇一起走进了会客大厅。后者的样子与我之前想象的大相径庭。我原以为我会看到威严的巴亚·巴亚奇特,而不是小小的比贝尔契。他向我伸出手,照相机的闪光灯把母亲和我吓了一跳。
“告诉布兰科先生你叫什么。”阿兹拉一边提示我,一边拽着我的胳膊伸向布兰科·乔皮奇。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只手的力度。
“阿……阿列克萨……阿列克萨……卡莱姆,我有点结巴。”
“跟他说说你觉得《驴子的岁月》怎么样。”母亲继续在我耳边私语。
“有什么用,他比我更清楚!”
就在这时,我想起父亲讲过的,肚脐下面的阵阵疼痛,以及俄语里把肚子叫作?ivot的事实。我抓着母亲的手,问题脱口而出:
“布兰科先生,为什么俄语里把肚子叫作?ivot?”
“因为在肚脐后面,是灵魂;而如果没有灵魂,就不叫生活。”
他把手指伸向我的肚脐,还挠我痒痒。我笑了。
“要当心……”他嘴里嘟哝着。
“我知道:不能让灵魂枯萎了!”
“噢,不!是不能让任何人吞了它!”
每次我离开萨拉热窝去国外,都要在贝尔格莱德中转。这是联系我与世界的纽带。我总是乐意在这里停留,在安娜姑妈家过夜。要想从机场到市中心去,就必须取道布兰科桥。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瞧见布兰科先生。我向他致敬,他也会回敬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兰科·乔皮奇从波斯尼亚的戈脉契山(14)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寻找他的叔叔。他没有找到人,他睡在了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桥上。多年以后,灵魂已被南斯拉夫的悲剧吞噬,他不得不尽快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为自己的主人公们感到担忧:尼科莱蒂纳·布尔萨奇、巴亚·巴亚奇特、叶祖哈克·耶泽奇、杜莱·达比奇。
假如一切都覆灭了,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扪心自问,却不能回答。
一天,布兰科·乔皮奇重新回到了他曾经在贝尔格莱德睡了一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向他致意。一个女人停下来,一脸困惑地盯着他走到桥的另一端,微微抬起胳膊向他致意。现在轮到布兰科停下了脚步,在跨过桥栏前,他瞥见了这个女人,也看到了她的手势,知道她想向他致意。他转身朝向她,回应了她,然后匆匆跃入萨瓦河。
(1) 卡尔·麦(Karl May, 1842—1912),德国著名探险小说家,也是被最广泛阅读的德文作家之一。——编者注
(2) 马托·罗夫拉克(Mato Lovrak,1899—1974),克罗地亚儿童文学作家。
(3) 波斯尼亚足球运动员。
(4) 阿西莫·费尔哈托维奇的绰号。
(5) 克罗地亚的一支职业足球队。
(6) 萨拉热窝的老市场及历史文化中心。——编者注
(7) 斯特万·布拉伊奇(Stevan Bulaji,1926—1997),黑山共和国著名作家。——编者注
(8) 奥勃洛莫夫,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主人公。——编者注
(9) 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因参加得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而牺牲。——编者注
(10) 克罗地亚评论员。
(11)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
(12) 贝尔格莱德管辖下的城镇。
(13) 法国心理学家。
(14) 位于波黑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