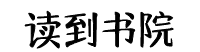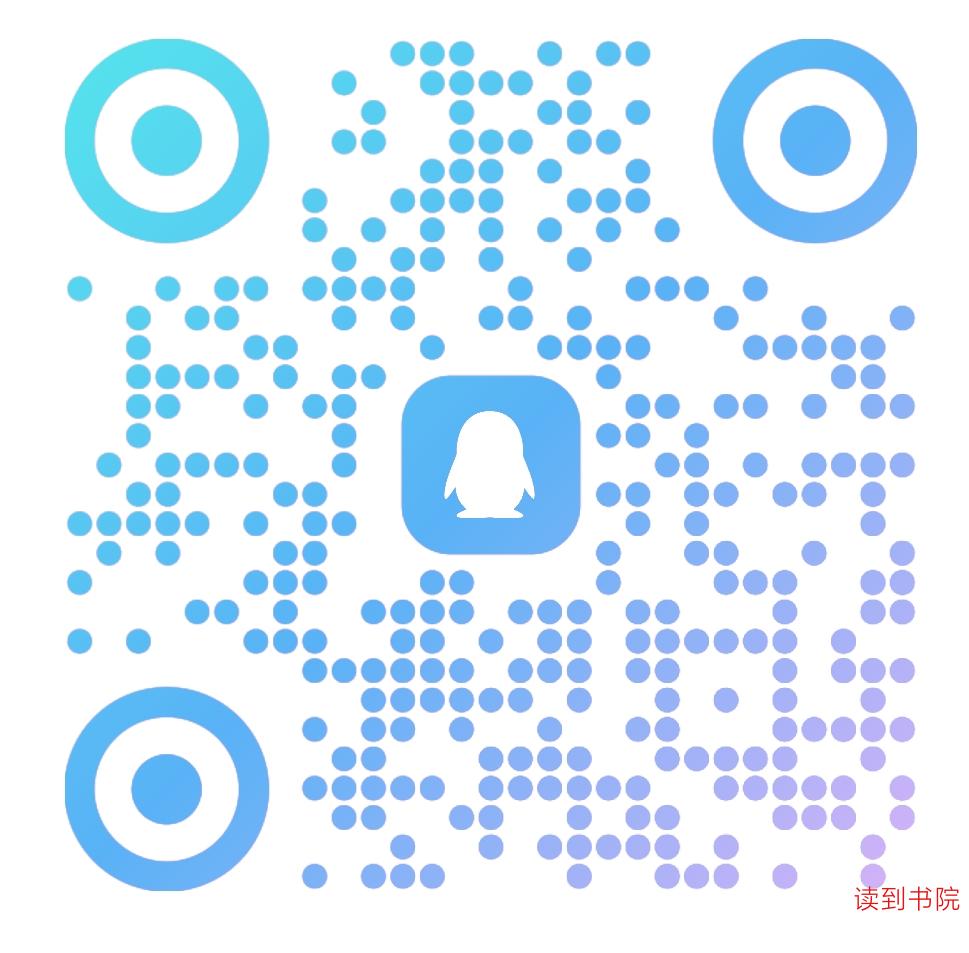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与两位法官商量了一阵,然后转身对着卡尔京金,脸上的神情分明在说,现在我们就要把案子的详情细节一五一十弄个明白。“农民西蒙·卡尔京金,”庭长将身体倾向左侧,开口说道。
西蒙·卡尔京金站起来,两手紧贴裤缝,全身前倾,面颊上的肌肉仍在不停地无声颤抖。
“您被指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伙同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和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皮箱中属于斯梅利科夫的钱款,然后取来砒霜,指使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放入酒中,让商人斯梅利科夫喝下,因而导致斯梅利科夫死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庭长说,并将身体歪向右侧。
“绝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侍候客人……”
“这些话您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绝对不,老爷。我只是……”
“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庭长平静但又坚定地重复道。
“我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跳到西蒙·卡尔京金跟前,用悲剧式的语调低声阻止他。
庭长露出此事到此结束的神情,将拿有公文的那只手的胳膊肘挪了一下位置,转身对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说:“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您被指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马夫里塔尼亚’旅馆,与西蒙·卡尔京金、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合伙盗窃了商人斯梅利科夫放在皮箱中的钱款和戒指,并将其分赃,此后为掩盖罪行,你们用毒酒将斯梅利科夫灌醉,致使他中毒身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没有任何罪过,”女被告坚定利落地说。“我连客房都没有进过……既然这个下贱女人进去过,那么事情就是她干的。”
“这些话您以后再说,”庭长照例温和而坚定地说。“那么您不承认自己有罪啰?”
“我没拿过钱,也没灌过酒,我连客房都没有进去过。要是有我在,我会撵走她。”
“您不承认自己有罪?”
“永远不承认。”
“很好。”
“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庭长开始问第三个被告,“您被指控带着商人斯梅利科夫的皮箱的钥匙,从妓院来到‘马夫里塔尼亚’旅馆,盗走皮箱内的钱款和戒指,”他像背书似的说道,同时将耳朵凑近左侧的法官,那个法官说,根据物证清单还缺一个玻璃瓶。“盗走皮箱内的钱款和戒指,”庭长又重复了一遍,“分赃后,您又与商人斯梅利科夫一道乘车来到‘马夫里塔尼亚’旅馆,您让斯梅利科夫喝下掺有毒药的酒,导致他死亡。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没有任何罪行,”她急促地说。“我原先怎么说,现在也怎么说:我没拿钱,我没拿钱,我没拿钱,我什么也没拿,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自己犯有盗窃二千五百卢布钱款的罪行?”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我什么都没拿。”
“那么您承认自己犯有给商人斯梅利科夫喝掺有齑粉的酒的罪行吗?”
“这我承认。不过我以为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是安眠药,喝了不会出什么事。我没有想到,也不想那样。对着上帝,我说一句:我不想那样,”她说。
“如此说来,您不承认自己犯有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但是您承认您给商人喝了掺有齑粉的酒了?”
“应当承认,不过我以为是安眠药。我给他喝只是想让他睡觉。我不想,也没有想到要那么干。”
“很好,”庭长说,他显然对审问取得的结果感到满意。“那么您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他说,身子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搁在桌子上。“您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一遍。您从实招供,可以从轻发落。”
玛斯洛娃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庭长,默不作声。
“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说。”
“事情的经过?”玛斯洛娃突然开口匆匆说道。“我来到旅馆,他们把我带到房间里,他就在那里,醉得很厉害。”她说到“他”字,脸上露出特别恐惧的表情,双眼瞪得大大的。“我想离开,他不放我走。”
她沉默不语,似乎失去了思路,或者是想起了另一件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有什么?后来我待了一会儿,就坐车回家了。”
这时候副检察官不自然地将一个胳膊肘支撑在桌上,欠起半个身子。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在得到副检察官肯定的答复后,他向副检察官示意,他把自己的提问权交给副检察官了。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原先和西蒙·卡尔京金熟悉吗?”副检察官说,眼睛并不看玛斯洛娃。
提问后他紧闭双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问题重复了一遍。玛斯洛娃恐惧地盯着副检察官。
“和西蒙?原先就熟悉,”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和卡尔京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常常见面吗?”
“交情怎么样?他常叫我去陪客人,这不是交情,”玛斯洛娃回答,眼睛不安地在副检察官和庭长之间来回打量。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京金单单找玛斯洛娃去陪客人,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起双眼,脸带刻毒狡猾的微笑,说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玛斯洛娃回答,她惊恐地四下环顾了一下,目光在涅赫柳多夫身上停留了一下。“他想找谁,就找谁呗。”
“莫非她认出来了?”涅赫柳多夫惊慌地想道,他觉得血直往脸上涌。但是玛斯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立即转过头,又带着惊恐的表情盯着副检察官。
“那么,被告否定自己同卡尔京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啰?很好。我再没有什么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即把支在桌子上的胳膊肘放下来,并提笔记录着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记,只是用笔将记录本上原先写着的字母描了描。不过他以前见过检察官和律师们都这样做:在提过巧妙的问题之后,在自己的发言稿上添上一些肯定可以击败对方的记号。
庭长没有马上追问被告,因为这时候他正在问戴眼镜的法官,是否愿意将事先准备好并且记在纸上的问题提出来。
“接下去又怎样呢?”庭长继续提问。
“我回到家里,”玛斯洛娃接着说,已经比较大胆地望着庭长一个人,“把钱交给女掌班,就躺下睡觉。刚刚睡着,我们的姑娘别尔塔就把我叫醒:‘快去吧,你那个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出门了,可是女掌班硬要我去。他就在这儿,”说到这个他字,她又带着明显的惊恐神色,“他不停地给我们姑娘们灌酒,后来他还想叫人去拿酒,可是他的钱用光了。女掌班信不过他。于是他就打发我去他住的旅馆。还告诉我,钱放在哪里,要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与左边的法官在悄声说话,没有听见玛斯洛娃说了什么,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全都听清了,他把她说的最后几个词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么,又怎样了呢?”他说。
“到了那里,一切都按他吩咐的做了:我走进房间。不是独自一人走进房间,还叫上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和她,”她指着博奇科娃说道。
“她胡说,我压根儿就没进去……”博奇科娃刚开口说,就被人阻止。
“当着他俩的面,我取了四张红票面的钞票,”玛斯洛娃皱着眉头不看博奇科娃,继续说道。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是否看见里边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发问。
副检察官刚向她提问,她就打了个哆嗦。玛斯洛娃虽不明白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但觉得他有意要害她。
“我没有数,看见里边都是百卢布票面的钞票。”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票面的钞票……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那么,怎么样,把钱带回去了?”庭长瞧着怀表,继续发问。
“带回去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来,”玛斯洛娃说。
“那您是怎样把齑粉掺进酒里拿给他喝的呢?”
“怎样拿给他喝?撒在酒里,就端给他喝了呗。”
“您为什么要给他喝?”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不放我走,”她沉默了一阵说。“我被他折腾得疲乏不堪。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能放我走就好了。我累极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也讨厌他。我们让他吃点安眠药,等他睡着,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吧。’我想,这种齑粉没有毒性。他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回到房间,他正躺在间壁后面,当即吩咐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子上的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自己一杯,他一杯,在他的杯子里撒了齑粉,就端给他喝。要是知道那是毒药,难道我会给他喝?”
“那么戒指怎么到您手的呢?”庭长问。
“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和他一到旅馆的房间,我就要走,他打我的脑袋,梳子也被打断了。我生气了,我要走。他摘下手指上的一枚戒指送给我,让我别走,”她说。
这时候副检察官再次欠起身子,又故作天真的姿态,请求允许他再提若干问题。得到允许后,他歪着竖在绣花领子上方的脑袋问:“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利科夫的房间里逗留了多长时间。”
玛斯洛娃又是一阵惊恐,不安地将目光从副检察官的脸上移到庭长的身上,急促地说:“记不得待了多长时间了。”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离开商人斯梅利科夫以后,是否去过旅馆的其他地方?”
玛斯洛娃想了一会儿。
“去过隔壁的一个空房间,”她说。
“您去干什么?”副检察官饶有兴趣地直接问她。
“去理理身上的衣服,等马车。”
“那卡尔京金是否也和被告一起进房间了?”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商人剩下一些上等白兰地,我们一起喝掉了。”
“嚄,一起喝掉了。很好。”
“那么被告和西蒙说过话没有?说了些什么?”
玛斯洛娃突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说了些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说。当时的情形我全都说了,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您要拿我怎么样?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再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并且很别扭地耸起双肩,急匆匆地将被告承认自己和西蒙一起去过空房间的供词,记在自己发言稿摘记本上。
接着是一阵沉默。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全都说了,”玛斯洛娃说,她叹了口气,坐下。
此后,庭长在公文纸上写了些什么,左边的法官悄声对他说了几句,于是他宣布休庭十分钟,自己赶忙站起来,走出法庭。原来,左边那位个儿高高的、长着一双和善的大眼睛的大胡子法官,刚刚对庭长说,他感到胃有点不舒服,想按摩按摩,再吃点药。他将此事告诉庭长,庭长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休庭。
在法官们之后,陪审员、律师、证人们也都站起身,他们意识到一件要案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于是心情愉快地到处走动。
涅赫柳多夫离开法庭来到陪审员议事室,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