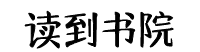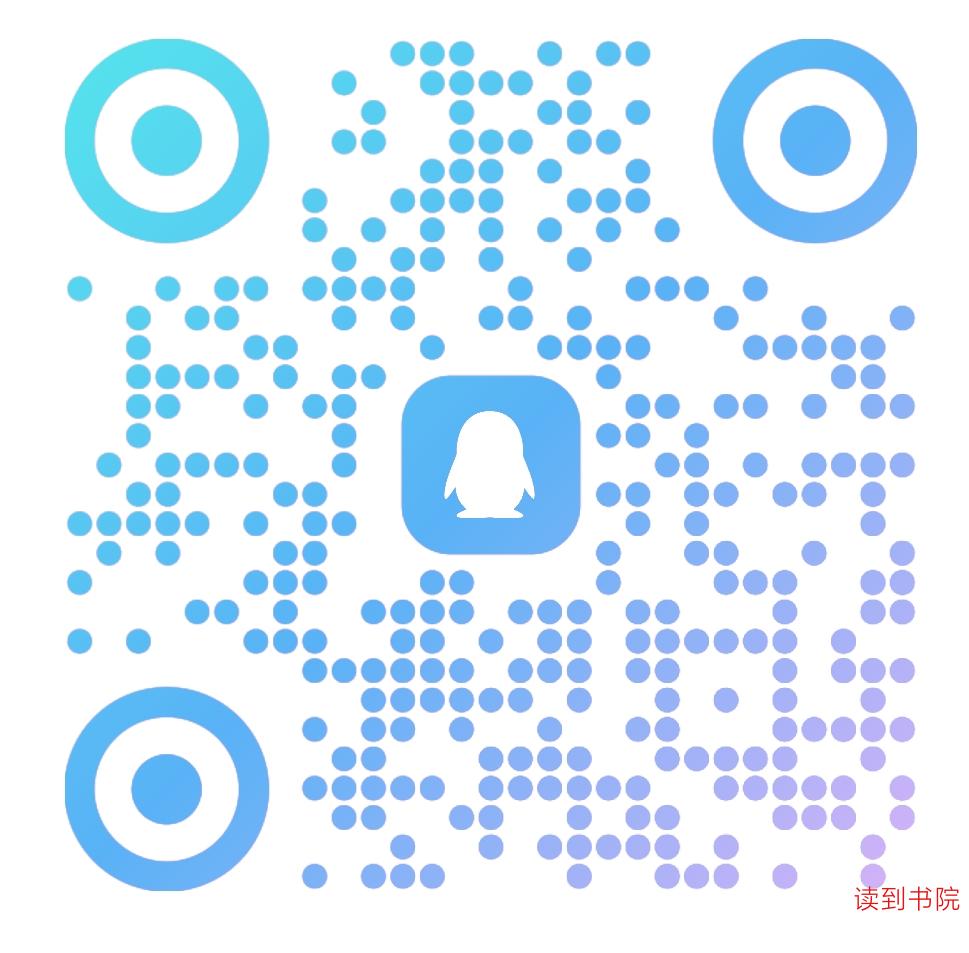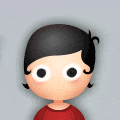庭长终于结束了发言,他用优雅的动作拿起问题纸,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站起身,他们都为可以离庭而高兴,一个个仿佛为什么事而害羞,手忙脚乱地一个紧跟一个地前往陪审员议事室。他们身后的门刚刚关上,一个宪兵便来到门边,从刀鞘里拔出军刀,将军刀靠在肩上,站在门边。法官们起身离开,被告们也被押走。
陪审员们一进陪审员议事室,第一件事照常是掏出烟抽起来。他们一进议事室,抽上烟,原先坐在法庭里自己位子上或多或少地体会到的自己姿势的别扭和虚伪便消失了,他们颇感轻松地坐在议事室内,立即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个姑娘没有罪,是一时糊涂,”心地善良的商人说,“应该从宽发落。”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应当凭我们个人的印象办事。”
“庭长作的总结发言很好,”那位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点睡着了。”
“关键在这儿,要是玛斯洛娃不与那两个茶房串通,他们就不可能知道有那么一大笔钱,”那个犹太人模样的店员说。
“照您这么说,钱是她偷的?”其中一个陪审员问。
“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喊道,“这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干的勾当。”
“他们都是好货,”上校说。
“她可是说过,她没进房间。”
“那您就去相信她吧。我一辈子都不会相信这个卑鄙可憎的贱女人。”
“可是您光是不相信也不解决问题呀,”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嘛。”
“在她手里又怎样?”商人反驳说。
“还有那枚戒指呢?”
“她可是说过,”商人又喊道,“那个身体粗壮的买卖人脾气暴躁,况且又喝多了,把她揍了一顿。后来嘛,很明白,又可怜她。就是说,喏,拿去吧,别哭了。那个人,据说,大概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八普特(1)重呢!”
“问题不在这里,”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插嘴说,“问题在于究竟是她,还是两个茶房唆使和策划了这件事?”
“光是茶房干不了。钥匙在她手里。”
这种东拉西扯、七嘴八舌的议论持续了很长时间。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请大家坐到桌边来讨论。请吧,”他说,并在主席位置上坐下来。
“这些姑娘都是坏蛋,”店员说。为了证明玛斯洛娃是主犯,他又讲述了他的一个同事在林荫道上被这种姑娘偷走怀表的事儿。
上校趁机讲了一个更为惊人的偷银茶炊的案件。
“诸位先生,请大家讨论正题,”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着桌面,说。
大家都住口不说了。提出的问题有以下这些:(一)克拉皮文县博尔基村三十三岁的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是否犯有下述罪行: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某城,为了掠夺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财,蓄意谋害他的生命,串通他人将毒药放进白兰地中让其喝下,结果导致斯梅利科夫死亡,然后盗走属于他的两千五百卢布的钱款和一枚钻石戒指?
(二)四十三岁的小市民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夫娜·博奇科娃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所述的罪行?
(三)二十七岁的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玛斯洛娃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所述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未犯第一个问题所述罪行,那么她是否犯有以下罪行: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某城的“马夫里塔尼亚”旅馆服务时,偷走该旅馆客人、商人斯梅利科夫客房内锁在皮箱中的两千五百卢布钱款,为此,她用随身带去的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皮箱的锁?
首席陪审员将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立刻作出回答。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他的确有罪,”认定他是投毒和盗窃的参与者。只有一位老年搬运工人不同意裁定卡尔京金有罪,他对所有问题的答复一律都是开脱。
首席陪审员心想,他不懂法律,于是向他解释说,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毫无疑问是犯了罪。但是搬运工说,他懂这些道理,但最好还是可怜可怜他们。“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说,于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关博奇科娃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解释之后,作出了“她没有罪”的答复,因为并无明显的证据证明她参与投毒,她的律师对此特别作了强调。
那位商人有意为玛斯洛娃开脱,坚持认为博奇科娃是整个案件的主谋。不少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首席陪审员为表示自己严格执法,声称没有根据证明博奇科娃参与投毒。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争论,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
对有关博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的答复是“她的确有罪”,但由于那位搬运工人的一再坚持,答复中加了一句“但应从宽发落”。
有关玛斯洛娃的第三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认为,她同时犯有投毒罪和掠夺罪,但是商人和上校、店员、搬运工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其余陪审员的态度摇摆不定。不过,首席陪审员的意见开始占优势了,特别是因为所有陪审员都已经疲乏,他们更愿意附和那种很快就能一致、因而能使他们大家脱身的意见。
根据法庭审讯的全部情况来看,同时根据涅赫柳多夫对玛斯洛娃的了解,他相信她既没有犯盗窃罪,也没有犯投毒罪,开始他还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认定。可是他看到,由于商人喜爱玛斯洛娃的姿色,这一点他毫不掩饰,为她作了拙劣的辩护,由于首席陪审员正是针对这一点作了反驳,更主要的,由于大家都疲乏了,争论的结果倾向于判她有罪,这时他想奋起反驳,可是他又害怕为玛斯洛娃说话,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大家立刻就都知道他和玛斯洛娃的关系。不过,他仍感到他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他应当起来反驳。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刚想开口说话,不料,在此以前一直沉默寡言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盛气凌人的权威口气所惹怒,突然开始反驳,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她偷了钱是因为她身上有钥匙。茶房难道就不能在她之后用事先配的钥匙打开皮箱上的锁吗?”
“是啊,是啊,”商人附和道。
“她不能拿那些钱,因为处在她当时的地位,她拿了钱没地方放。”
“我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商人证明说。
“也可能是因为她到旅馆里来引发了茶房的歹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作案,事后把事情全都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话时火气很大,这种火气也传给了首席陪审员。因此,首席陪审员特别执拗地坚持自己的相反意见。可是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话令人信服,以致大部分人认定,玛斯洛娃并未参与盗窃钱款和戒指,戒指是商人赠送给她的。说到她是否参与投毒时,那个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说,应该认定她无罪,因为她毫无必要毒死商人。首席陪审员说,不能裁定她无罪,因为她自己供认给他下过齑粉。
“是下过药,但是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用鸦片也能毒死人,”喜欢打岔的上校说,于是他趁机说起他的内弟媳妇服鸦片自尽,要不是附近有医生,抢救及时,她肯定死了。上校说得如此动情、自信、得体,谁也没有勇气去打断他的话,只有那个店员受了他的感染,决定打断他的话,以便说一说他的故事。
“有些人习惯了,”他开口说道,“一次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是上校不允许别人打断他的话,接着又说起他内弟媳妇服了鸦片的后果。
“唉,诸位先生,已经四点多了,”其中一个陪审员说。
“这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裁定她有罪,但没有掠夺的企图,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行吗?”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很满意自己得胜,于是同意了。
“不过要从轻发落,”商人补充说。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搬运工人坚持要裁定“她无罪”。
“结果是一样的,”首席陪审员解释道,“既没有掠夺的企图,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就无罪了。”
“就这样办吧,再要求从轻发落,如有漏洞,后一条也能统统堵上,”商人喜滋滋地说。
大家都累了,争辩得糊涂了,谁都没有想到要在答复中补上一句:“是的,但无意谋害性命。”
涅赫柳多夫激动不安,竟然也没发现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记录下来,送到法庭。
拉伯雷(2)描写过一个法学家,人家找他办案,他先是向人家指点各种各样的法律,再读上二十页毫无意义的拉丁语法律条文,然后让打官司的人掷骰子,看看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那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那就是被告有理。
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作出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表示同意,而是因为一,庭长作了如此冗长的总结发言,这次却偏偏漏掉了他以往一直说的、他们在回答问题时正是可以说的:“是的,她犯有罪,但无意谋害性命”;二,上校说的关于内弟媳妇的故事太长、太枯燥;三,涅赫柳多夫太激动,没有发现遗漏了关于并无意谋害性命这一说明,他以为写了“没有掠夺的企图”的说明,就消除了判罪的可能;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不在议事室,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正出去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太疲劳,都想早点脱身,所以都同意这个可以尽快结案的决定。
陪审员们按了铃。站在门口的宪兵将出鞘的军刀插回刀鞘,并让到一旁。法官们都已就位,陪审员们一个跟着一个回到法庭。
首席陪审员神态庄严地拿着那张纸。他走到庭长面前,把纸交给庭长。庭长看了一遍,显然感到惊讶,他摊着双手,转身与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惊讶的是,陪审员们写了“无掠夺的企图”这第一个保留条件之后,竟没有写“无意谋害性命”这第二个保留条件。这样一来,根据陪审员这个决定,玛斯洛娃既未偷窃,也未掠夺,同时又毫无明显目的毒死一条人命。
“您瞧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庭长对左边那位法官说。“要知道这得判她服苦役,可她却无罪。”
“哼,她怎么无罪?”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实在是无罪,依我看,这种情形适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如果法庭认为裁决不当,可以取消陪审员的裁定。)“您看怎么样?”庭长问心地善良的法官。
善良的法官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看面前公文纸的页码,将数字加起来,结果不能被三整除。本来他打算,如果能被三除尽,他就同意,现在尽管不能除尽,出于善良的天性,他也同意了。
“我也是这样想,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气冲冲的法官。
“无论如何不同意,”他断然回答。“报界一直在说陪审员们总是为罪犯开脱;如果法官们也为罪犯开脱,他们会怎么说?我无论如何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怀表。
“很遗憾,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把问题纸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倒换着双脚,清了清嗓子,将问题和答案读了一遍。法庭上所有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还有副检察官,全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被告们毫不焦急地坐着,他们显然不理解答案的含义。大家又都坐下,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给几个被告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副检察官对于处置玛斯洛娃的意外成功喜不自禁,他将这个成功归功于自己出色的口才,他在法典里查了查,欠起身,说:“我认为,西蒙·卡拉京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判处,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判处,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判处。”
所有这些刑罚都是依法所能判处的最重的刑罚。
“法官退庭商议判决,”庭长站起身,说。
大家跟着站起来,仿佛完成了重大的事业,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走出法庭,或者在庭内来回走动。
“老兄,我们可是闹出丢脸的丑事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当时首席法官正向他说着什么。“我们把她搞去服苦役了。”
“您在说什么?”涅赫柳多夫扬声叫道,这一次他根本没察觉这位教师令人讨厌的不拘礼节的态度。
“不是吗,”他说。“我们在答案中没有写上:‘她犯有罪,但并无意谋害性命。’书记官刚才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本来就这样裁定的,”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开始争辩说,事情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她既然没拿钱,也就不可能有意谋害性命。
“要知道,在离开议事室之前,我将答案读过一遍,”首席陪审员辩白道。“当时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那时我离开议事室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你们怎么也打呵欠啦?”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涅赫柳多夫说。
“这就是没有想到的结果。”
“这件事还可以纠正,”涅赫柳多夫说。
“哦,不行了,现在全完了。”
涅赫柳多夫望着那些被告。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可是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端坐在栏杆后边,坐在士兵面前。玛斯洛娃不知为什么事还微笑着。涅赫柳多夫心中一种可恶的情绪在活动。在此以前,他以为她会被判无罪释放,留在这座城市,他正在犹豫,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处理与她的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苦役和西伯利亚一下子消除了与她有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受伤未死的小鸟不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到它。
【注释】
(1)旧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2)拉伯雷(1494—1553),法国人文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