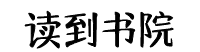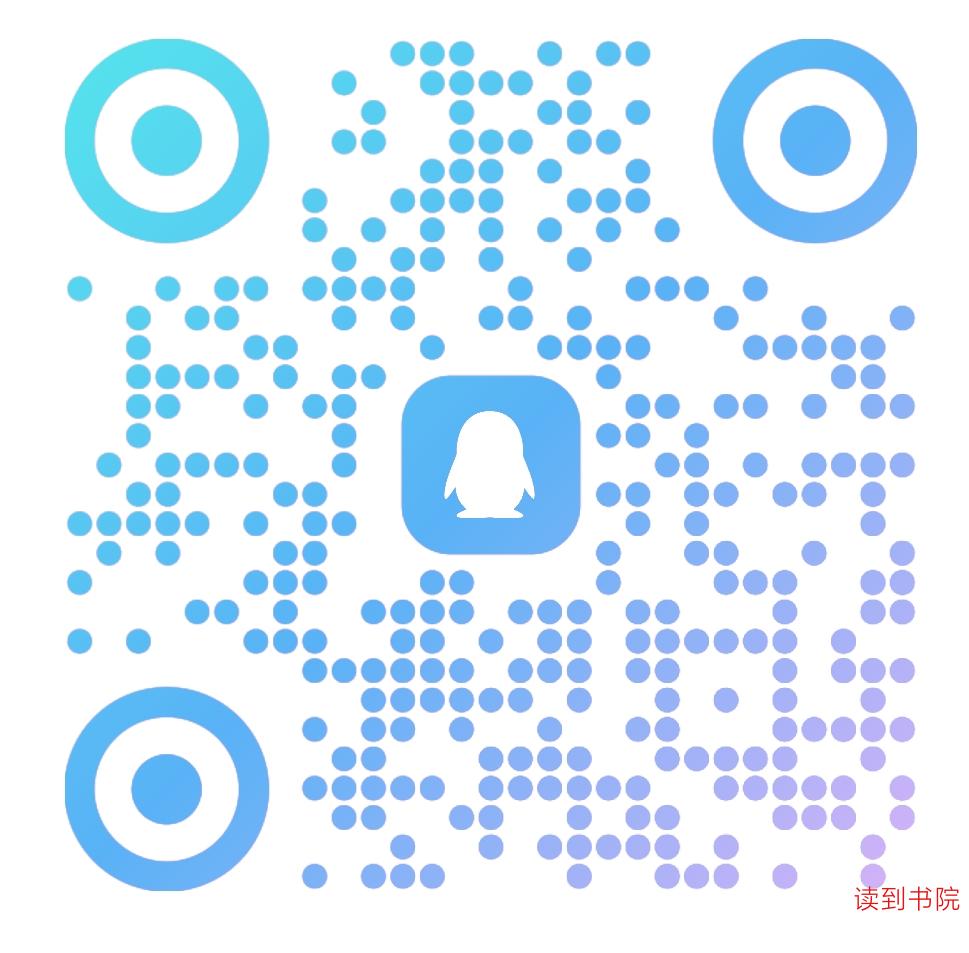玛斯洛娃回头望了望,抬起头,挺起胸,脸上露出涅赫柳多夫所熟悉的那种恭顺的神情,走到铁丝网旁边,挤在两个女犯之间,惊奇而询问地盯着涅赫柳多夫,没有认出他来。
但是她根据穿着看出,他是一个富人,于是面露微笑。
“您找我?”她说,将眼睛微微斜视的笑脸贴近铁丝网。
“我想见见……”涅赫柳多夫不知道该说“您”还是“你”,不过他决定说“您”。他说话的声音不比平时高。“我想见见您……我……”
“你别跟我说废话,”他身旁那个衣衫破烂的人吼道,“你拿没拿?”
“跟你说,人都快要死了,还要说什么?”对面有个人喊道。
玛斯洛娃听不清涅赫柳多夫说的话,但他说话时的面部表情突然使她想起了他。可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前额痛苦地起皱了。
“您说什么,听不见,”她眯着眼睛喊道,额头的皱纹越来越深了。
“我来……”
“是啊,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来认错,”涅赫柳多夫想道。一想到这一点,泪水就涌入眼眶,哽住了喉咙,于是他手指抓住铁丝网网眼,说不下去了,竭力克制着没有哭出声来。
“我说,你为什么要管不该管的闲事……”这边有人喊道。
“你该相信上帝,我真不知道,”那边的一个女犯喊道。
玛斯洛娃看到涅赫柳多夫激动的样子,终于认出是他。
“好像是,可是我认不出来,”她喊道,眼睛不看他,突然涨红的脸变得更阴沉。
“我是来请求你宽恕的,”他大声地喊道,声调呆板,就像在背书似的。
喊出这句话之后,他觉得羞惭,于是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过他立即又想到,如果他感到羞惭,那就更好,因为他应当承受这种耻辱。于是他继续大声高喊。
“请你宽恕我,我很对不起……”他又喊道。
她站着一动不动,乜斜的目光一直盯着他。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离开铁丝网,竭力克制着翻腾起伏的胸膛,没有哭出声来。
将涅赫柳多夫打发到女探监室来的副典狱长显然对他产生了兴趣,于是也来到这里。看见涅赫柳多夫并未站在铁丝网旁边,便问他为什么不和他要找的那个女犯说话。涅赫柳多夫擤了擤鼻子,振作起精神,尽量摆出镇定的样子,回答:“无法隔着铁丝网说话,什么都听不见。”
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会儿。
“那好吧,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会儿。”
“玛丽亚·卡尔洛夫娜!”他转身对一个女看守说。“把玛斯洛娃带出来。
”过了一分钟,玛斯洛娃从旁边一扇门里走出来。她迈着轻柔的步子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望着他。像前天那样,几绺鬈曲的黑发露在外面,浮肿苍白的脸略带病态,但仍显得漂亮和镇定,微肿的眼睑下那双乌黑发亮的斜眼睛显得格外明亮。
“可以在这里说话。”副典狱长说毕,就走到一旁。
涅赫柳多夫走近靠墙放着的长凳。
玛斯洛娃询问地望了一眼副典狱长,然后仿佛惊奇似地耸了耸肩膀,跟着涅赫柳多夫走近长凳,理了理裙子,在他身边的凳子上坐下。
“我知道,您很难宽恕我,”涅赫柳多夫开口说道,不过他又停下,觉得泪水妨碍他说下去,“可是,如果过去的事已无法纠正,那么我现在要尽我一切力量去做。您说吧……”
“您是怎样找到我的?”她并不回答,反而问道,那双微微斜视的眼睛对他似看未看。
“我的上帝!帮帮我吧。教教我该怎么办!”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瞧着她那张变化很大、现在令人不快的脸。
“前天审问您的时候,我是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吗?”
“是的,没认出来。我没有空认人。我根本没看,”她说。
“不是有个孩子吗?”他问,觉得脸上通红。
“感谢上帝,当时就死了,”她简短、凶狠地回答,目光离开了他。
“怎么死的,什么原因?”
“我自己病得差一点死了,”她眼睛不抬地说道。
“两个姑妈怎么会放您走?”
“谁肯留怀小孩的女仆?发觉了,就赶出来了。有什么好说的,我什么都记不得,全忘了。那件事全都了结了。”
“不,没有了结。我不能丢开这件事不管。就是现在我也想赎罪。”
“没什么可赎的,过去的事过去了,”她说。他万万没想到,这时她突然令人不快地、献媚而又怜悯地朝他微微一笑。
玛斯洛娃怎么也想不到会见到他,特别是现在,在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最初一刻他的出现使她震惊,迫使她想起她从未想过的往事。在最初一刻她隐隐约约想起了感情和思想的那个新的神奇的世界,那个爱着她、也被她爱着的可爱的青年,为她打开的新的神奇的感情和思想的世界,接着她又想起了他那无法理解的残酷,想起紧随那美妙的幸福之后,而且由此产生的种种屈辱和苦难。她感到痛苦。可是她无法理解这件事,于是她现在也像以往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回忆从心中驱除,竭力用一种特别的淫荡生活的迷雾遮盖这些回忆,现在她的确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刻,她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与那个她曾经爱过的青年联系在一起,可是后来她发现这样做太痛苦,她也就不再将他和那个青年联系起来。现在面前这位穿着洁净、胡子上洒过香水、保养得很好的先生,对她说来已不是她曾爱过的涅赫柳多夫,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享用一下像她这样的女人的身体的那些人之中的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也必须尽可能地利用那些人为自己谋求利益。因为这个原由,她对他献媚地一笑。她沉默了一阵,心中盘算着怎样从他身上捞到好处。
“那些事全都了结了,”她说。“现在我被判服苦役。”
她在说出这个可怕的词的时候,嘴唇都在哆嗦。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无罪的,”涅赫柳多夫说。
“我当然没罪。我怎么会是贼或强盗?我们这里的人说,事情全靠律师,”她继续说。“她们说,得上诉。不过,据说得花很多钱……”
“对,一定得上诉,”涅赫柳多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
“别舍不得钱,请好律师,”她说。
“只要办得到,我都要做。”
一阵沉默。
她又露出那种笑容。
“我想求您……给点钱,要是能够。不多……十卢布,用不着更多,”她突然说。
“行,行,”涅赫柳多夫难为情地说,同时掏出钱夹。
她朝正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副典狱长匆匆瞟了一眼。
“别当着他的面给,等他走开给,要不会被没收的。
”副典狱长刚转过身去,涅赫柳多夫便掏出钱夹,可是还没来得及将十卢布的纸币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俩。涅赫柳多夫就把钱攥在手心。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女人,”他寻思道,望着这张曾经那么可爱、现在却已被玷污的臃肿的脸。她那双斜视的黑眼睛闪着不正经的光,注视着副典狱长和攥着纸币的那只手。他心中有一刻动摇了。
昨天夜里说过话的那个诱惑者又在涅赫柳多夫心中说话了,像以往一样,它千方百计诱使他不去考虑应该做什么,而只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怎么做才有利。
“你对这个女人毫无办法,”这个声音说,“你只是往自己脖子上挂石头,这块石头会使你淹死,妨碍你成为对别人有益的人。给她钱,把手头所有的钱都给她,然后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他暗自想道。
可是他立即就感觉到,现在,就是在此刻,他的灵魂发生着某种重大的变化,他的内心活动此刻仿佛处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任何微小的努力都可能使天平向这边或那边倾斜。于是他就作了这种努力,召唤他昨天感觉到在自己心中的那个上帝,那个上帝立即在他心中作出响应。他决定现在把一切都对她说。
“卡秋莎,我是来向你请求宽恕的,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宽恕我了,以后你会不会宽恕我,”他说,突然对她改称“你”。
她并不听他说,而是一会儿瞧瞧他的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到副典狱长转过身去,她迅速向他伸出手,抓过那张纸币,塞到腰带里。
“您说的真奇怪,”她说,他觉得她在蔑视地冷笑。
涅赫柳多夫感觉到,她心中有一种直接敌视他的情绪,卫护着她目前的心态,妨碍他深入她的内心。
可是事情也真奇怪,这不仅没有排斥他,反而以某种新的特殊的力量将他吸引到她身边。他感到他有义务在精神上唤醒她,但也感到这件事极为困难;可正是这种困难本身吸引了他。他现在对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以往无论对她还是对别人都不曾有过,这种感情里丝毫没有私心:他不想从她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一心只希望她不再是目前这种状态,希望她觉醒,成为她从前那样。
“卡秋莎,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从前在帕诺沃的你……”
“何必提那旧事,”她冷淡地说。
“我回忆往事是为了改正错误,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始说道,他刚要说他要娶她,可是遇到了她的目光,目光中有一种令人可怕的、粗野的、排斥的意味,使得他没能说下去。
这时候探监的人往回走了。副典狱长走到涅赫柳多夫身边说,探监的时间结束了。玛斯洛娃站起来,驯服地等候别人来把她带走。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但是您瞧,现在不能说了,”涅赫柳多夫说,并伸出一只手。“我还会来。”
“好像全都说完了……”
她也伸出手,但没有握他的手。
“不,我要争取和您再见面,在可以说话的地方,那时候我将告诉您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您,”涅赫柳多夫说。
“行啊,您来吧,”她说,脸上流露出要讨男人喜欢的微笑。
“对于我,您比姐妹还要亲,”涅赫柳多夫说。
“真奇怪,”她又重复这个词,并摇了摇头,回到铁丝网那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