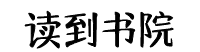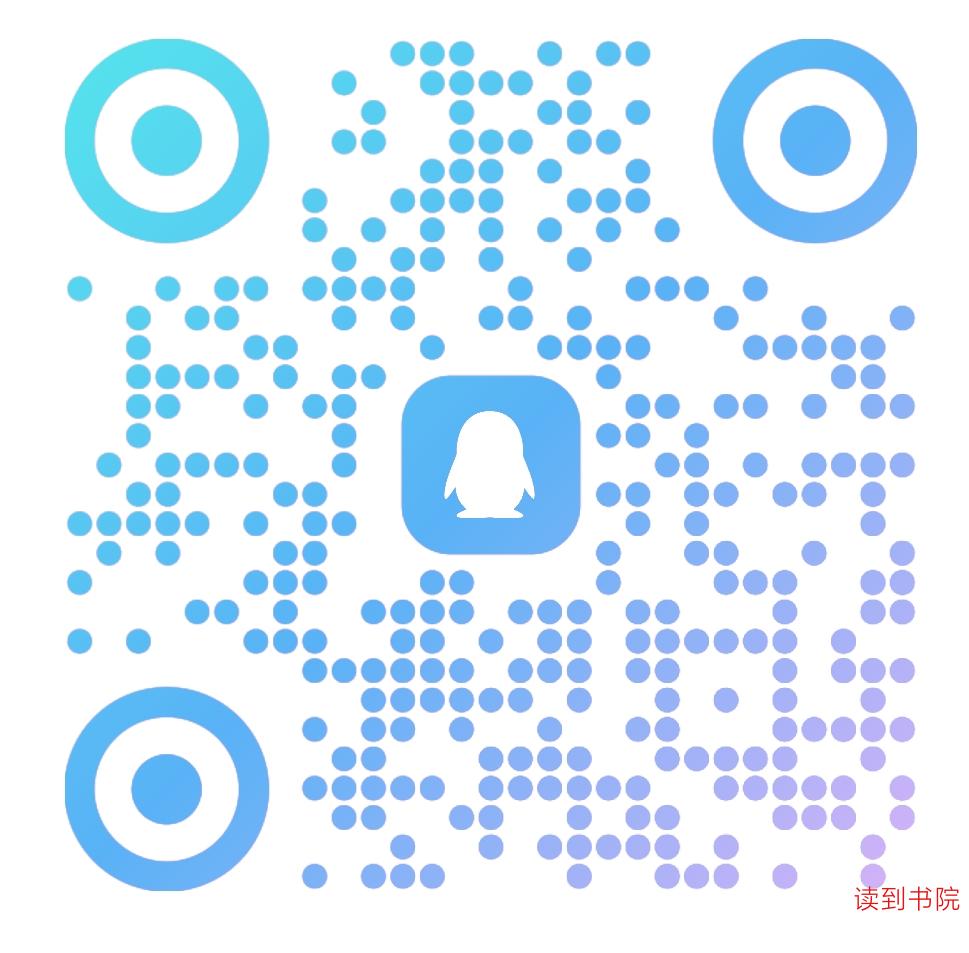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拉响门铃,想到玛斯洛娃今天的心情会怎么样,想到她与她同监的犯人会对他保守什么秘密,不由得心慌意乱,胆战心惊。他向一个出来开门的看守说,要见玛斯洛娃。看守进去查对以后对他说,她现在在医院里。涅赫柳多夫就到医院去了。医院的看门人,一个很面善的小老头马上就放他进去,在问清他要见什么人以后,就领他到儿科病房。
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的年轻医生走到走廊里,板起面孔问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这个医生对犯人还算体恤,所以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他担心涅赫柳多夫要他做违反规章的事情,此外,他希望表明自己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于是装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人,是儿科病房,”他说。
“我知道,不过有一个从监狱里调来的助理护士在你们这儿。”
“对,这里有两个。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
“我和其中的一个,叫玛斯洛娃的很熟悉,”涅赫柳多夫说,“我想见见她,我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提出上诉。我还想把一件东西交给她,这不过是一张照片。”涅赫柳多夫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
“好吧,这可以,”医生说,态度缓和下来。他转过身去对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说,要她把当助理护士的女犯人玛斯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会?要不,到接待室去?”
“谢谢您,”涅赫柳多夫说,他看到医生对自己态度有了转变,就趁机问他,玛斯洛娃对医院的工作是否感到满意。
“还好,由于想到过去的生活条件,所以她在这里工作得不错,”医生说。“看,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身后跟着玛斯洛娃。她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三角巾,盖住头发。她一见到涅赫柳多夫,脸上泛起了红晕,迟疑不决地停住了脚步,接着皱起双眉,垂下眼睛,轻捷地沿着走廊里铺着的花条布地毯走来。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本不想把手伸给他,后来还是伸出来,脸也涨得越来越红。上一次他们谈话,她发了脾气又向他道歉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现在他估计她的心情会跟上次一样。可是今天她完全变了,脸上露出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涅赫柳多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了刚才对医生所说的话,说他要到彼得堡去,然后交给她一个装着从帕诺沃带来的照片的信封。
“这张照片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是很早以前拍的,也许您会喜欢的。您收下吧。”
她微微抬起乌黑的眉毛,乜斜着眼睛惊奇地看着他,好像在问为什么给她这个。然后她默默地拿起信封,把它塞进围裙里。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涅赫柳多夫说。
“是吗?”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涅赫柳多夫问。
“还可以,很好,”她说。
“不太苦吧?”
“不,还可以,我还没有习惯。”
“我为您感到高兴,这儿总比那儿好。”
“那儿是什么地方?”她说,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儿,在监狱里,”涅赫柳多夫急忙说。
“这儿好在哪里?”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比较好,跟那儿的人不一样。”
“那儿也有很多好人,”她说。
“我为梅尼绍夫的案子忙乎了好久,希望能把他们放出去,”涅赫柳多夫说。
“愿上帝保佑他们。这老太太人真好,”她再一次说了自己对老太太的看法,然后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到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审理,我希望他们能撤消原判。”
“撤消不撤消现在反正都一样,”她说。
“您说‘现在反正都一样’是什么意思?”
“说说罢了,”她说,用探问的目光瞅了瞅他的脸。
涅赫柳多夫从她的话里和她的眼神里似乎看出,她想知道他是否还坚持自己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从而改变了他的决定。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觉得反正都一样,”他说,“然而对我说来,判您无罪也好,有罪也好,倒确实是一样的。不管怎样,我都准备按照您说的去做,”他坚定地说。
她抬起头,一对斜睨的黑眼睛看着他,又好像不在看他,她的整个脸上漾开了愉快的笑容。可是她说的话和她眼神里所表示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您不该说这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该说的都说了,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她说,好容易忍住没笑出来。
病房里吵吵嚷嚷,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
“好像在叫我,”她心神不安地回头看看说。
“好,那么再见,”他说。
她装作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没有握别就转过身去。她竭力想掩饰自己内心的高兴,匆匆地沿着走廊上的花条布地毯离开了。
“她究竟怎么啦?她现在怎么想的?她现在的心情怎样?她是想考验我,还是确实不肯原谅我?她是不能把自己所想的和感受到的一切都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心肠软下来了,还是怀恨在心?”他一再问自己,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答案。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把他和她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他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联结给他带来了欢欣,也给他带来了平静。
玛斯洛娃回到设有八张儿童病床的病房里,就按照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在铺床单的时候,由于腰弯得太低,她脚下一滑,差一点跌一跤。一个脖子上绕着纱布、正在康复的小男孩瞧着她,笑了起来。玛斯洛娃再也忍不住了,一屁股坐到床边上,放声大笑起来。有几个孩子也被她引得哈哈大笑。那个护士生气地对她喝道:“笑什么!你当是还在以前待的地方!快拿饭去!”
玛斯洛娃马上抿拢嘴巴,拿起餐具,到吩咐她去的地方去了。可是临走,她和那个绕着纱布、被禁止发笑的男孩互相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一天里,只要玛斯洛娃看见旁边没有人,总要偷偷地把照片从信封里抽出一半欣赏一下。可是晚上值完班以后,独自一人待在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同住的房间里,她才从信封里拿出照片,温情脉脉地、久久地凝视着,端详照片上每一个细节、他们的面庞、他们的装束、阳台的台阶和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的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个姑妈的脸。她拿着这张褪色发黄的照片,对那时的她总是百看不厌;那时她多么年轻,多么漂亮,额头上飘着鬈发。她看得那么出神,竟然没有发现和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来。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那个心眼很好的胖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着照片,说,“这个人就是你吗?”
“还能是谁呢?”玛斯洛娃看着同伴的脸,笑着说。
“这人是谁?是他吗?这人是不是他母亲?”
“那是他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我来了?”玛斯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永远也认不出来。你的脸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想,离现在有十来年了吧。”
“不是十来年,是隔了一辈子,”玛斯洛娃说,她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消失了,脸色变得阴郁,两条眉毛之间嵌进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是啊,很轻松,”玛斯洛娃闭上眼睛,摇着头,重复着她的话说,“比服苦役还不如。”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天天都是这样。”
“为什么不抛开这种生活呢?”
“想抛开,可是做不到。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玛斯洛娃说着站起身来,把照片往小桌子的抽屉里一塞,强忍住愤懑的泪水,跑到走廊上,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她望着照片,觉得自己还是照片上的模样,她幻想着她那时候多么幸福,如果现在能和他在一起,那又该是多么幸福啊。同伴的话使她想起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当年在那边的生活,那种可怕的生活,她当时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直到现在她才清晰地回忆起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别是那个谢肉节的夜晚,她等候着一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记得那天晚上她穿了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扎了一个花蝴蝶结,她喝得醉醺醺的,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到半夜两点才把客人一个个送走。她趁跳舞的间隙,坐到那个瘦骨嶙嶙、脸上长着粉刺的为小提琴伴奏的女钢琴师边上,向她诉说自己艰难的生活。那女钢琴师也说她为自己的境况感到苦恼,想改变一下。这时,克拉拉走了过来。她们三个人突然决定要抛弃这种生活。她们认为今晚总该结束了,就打算各自回房去。那知喝得醉醺醺的客人们又在前厅里吵吵嚷嚷起来,小提琴师拉起了前奏曲,女钢琴师敲响了琴键,弹起了卡德里尔舞曲第一节——一首欢快的俄罗斯歌曲。一个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的身材矮小的男人,头上冒汗,满身酒气,不住地打嗝,等到舞曲奏到第二节时,就脱去外套,走到玛斯洛娃的面前,一把搂住她的腰。另一个留着络腮胡子、也穿着燕尾服的胖子(他们刚刚参加过另一个舞会)搂住克拉拉。他们不停地跳啊,转啊,叫啊,唱啊……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二年,三年。一个人怎么会不变呢!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她想骂他,责备他。她后悔今天错过了机会,没能再对他说一次,她知道他的为人,决不会对他让步,不容许他再从精神上利用她,就像他过去从肉体上利用她一样,也不容许他把她当作他的宽宏大量的对象。她既怜惜自己,又徒然地责备他,她真想痛快地喝杯酒来浇灭心中的痛苦。如果她现在是蹲在监狱里,她就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只有从医士那儿才能弄到酒。可是她怕那个医士,因为他总是对她纠缠不休。她讨厌跟男人们交往。她在走廊里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就回到小房间里去了。她没有和同伴答话,独自一人为自己的不幸身世暗暗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