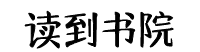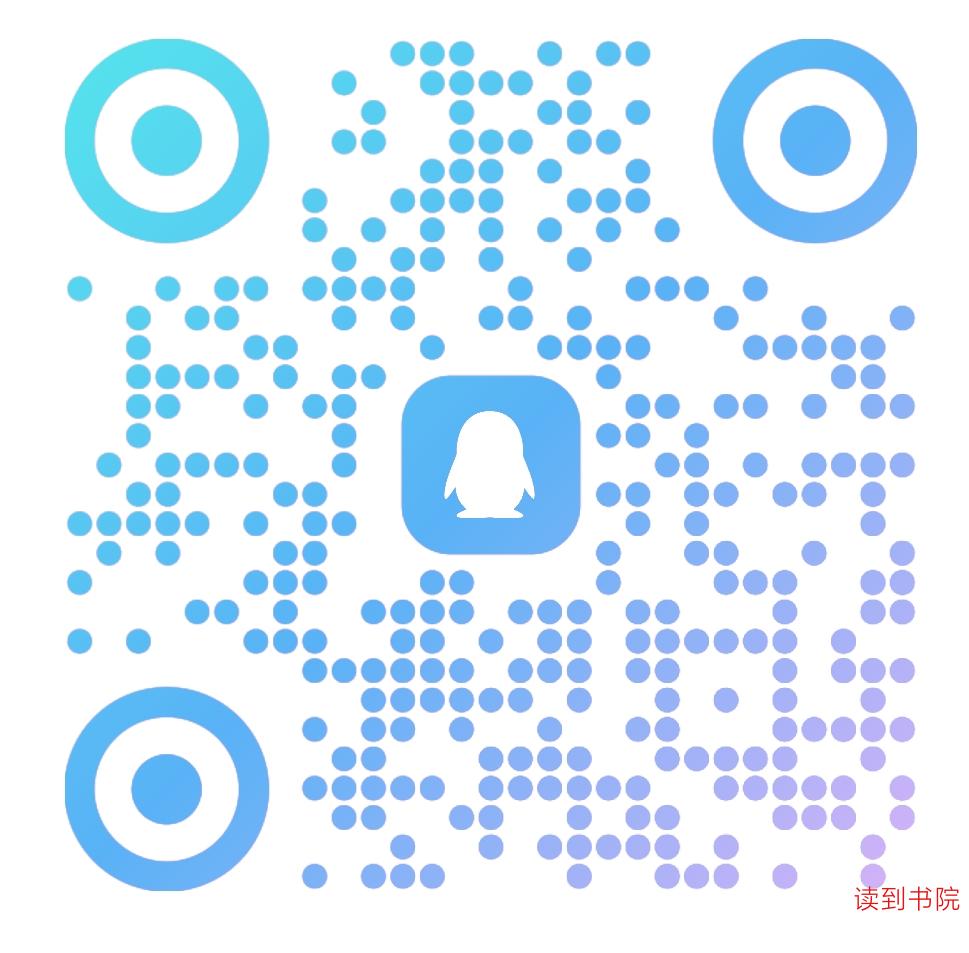涅赫柳多夫和律师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开始对涅赫柳多夫讲述枢密官们谈论的某局局长的事。那个局长的丑事被揭露以后,非但没有依法判服苦役,反而被调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件事的经过和全部丑闻以后,更加津津有味地讲起另一件事:一些高官显贵吞没了一笔准备建立一座纪念碑的筹款,今天早上他们曾路过那里,纪念碑至今还没有竖起来。律师还讲了某人的情妇做证券交易,赚了好几百万卢布,还讲到有个人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去,另一个人又把她买进来。律师还讲到政府的高级官员如何营私舞弊,罪行累累,非但没有坐牢,却仍然稳坐交椅。律师肚子里的这种故事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他讲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些故事充分说明他作为一名律师的取财之道,比起彼得堡的达官贵人要正当得多,清白得多。涅赫柳多夫没有听他说完这些官场丑闻,就向他告辞,叫了一辆马车回河滨街的姨妈家去了。律师不禁感到十分惊讶。
涅赫柳多夫愁肠百结。他所以愁肠百结,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斯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和玛斯洛娃共生死同命运的不变决心难以实现。此外,律师兴致勃勃讲述的那些为非作歹的丑闻,以及不时浮现在他眼前的谢列宁怀有敌意的、冷峻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目光,而以前他是那样可爱、坦诚、高尚,这一切都使涅赫柳多夫更加郁郁不乐。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带点鄙夷的神情将一张字条交给他,说这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张字条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道,她特意前来向她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此外,她还恳求他务必到她们那里去一次,她们住在瓦西里岛第五街某号。她还写道,维拉·叶夫列莫夫娜非常希望他去。希望他不用担心她们会唠唠叨叨地谢他,使他心烦意乱:她们不会向他当面道谢,只是想见见他。如果他有空,请他明天早上去一次。
还有一张字条,是涅赫柳多夫的老同学、宫廷侍从武官博加特廖夫写的。涅赫柳多夫曾经托他亲自把他以教派信徒名义写的状子呈给皇上。博加特廖夫用粗犷有力的笔迹写道,他会不负重托,将状子面呈皇上,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涅赫柳多夫先去找一下能够左右这个案子的人,向他求求情,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逗留的几天中得到的印象使他感到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在他看来,就像青年时代的梦想,如果人们带着它走进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大失所望。不过,他既然到了彼得堡,他认为有责任去执行原来的计划。他决定先去看望博加特廖夫,然后按照他的建议,登门拜访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浏览一遍,这当儿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叫听差来请他上楼去喝茶。
涅赫柳多夫说他马上就去,于是把状子放入皮包,就到姨妈那儿去了。上楼的时候,他望了一眼窗外,忽然看见玛丽埃塔的一对栗色马停在街上,不禁喜出望外,差一点笑出声来。
玛丽埃塔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穿了一件亮丽花哨的连衣裙。她坐在伯爵夫人旁边,手里端着茶杯,一对美丽而含笑的眼睛闪闪发亮,正唧唧喳喳地说着话。涅赫柳多夫走进去的时候,玛丽埃塔刚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而且是一句既令人发笑、又极不体面的脏话。涅赫柳多夫单凭这笑声就听得出来,它引得为人敦厚、嘴上长毛的伯爵夫人笑得胖胖的身子前俯后仰,而玛丽埃塔显出一副特别调皮的样子,撇着略带笑意的嘴,歪着容光焕发、喜溢眉梢的脸蛋,默默地瞅着伯爵夫人。
涅赫柳多夫从片言只语中听出,她们谈论的是当时流传在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西伯利亚新省长的逸事。玛丽埃塔就是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你要让我笑死了,”她咳嗽着说。
涅赫柳多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来。他刚想批评玛丽埃塔举止轻浮,她立刻变了脸色,甚至整个心情都变了,因为她发现涅赫柳多夫板着面孔,满脸不高兴。玛丽埃塔自从看到他以后,为了讨他喜欢,总想装得一本正经。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她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寻求新的目标。她这样说倒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她此时的心情确实和涅赫柳多夫一样,虽然她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涅赫柳多夫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便讲述了在枢密院上诉失败的经过和见到谢列宁的事。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心灵!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1)!一颗纯洁的心灵!”两位太太引用了谢列宁在上流社会中享有的美称来赞扬他。
“他妻子怎么样?”涅赫柳多夫问。
“他妻子?我不想说她坏话。可是她不了解丈夫。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她用发自内心的同情的口气问,“这真可怕,我真为她难过,”她叹了口气补充说。
他皱起眉头,打算改变话题,就谈起了舒斯托娃,亏得玛丽埃塔帮忙,才从要塞里放出来。涅赫柳多夫向她表示感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好话。他还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全家之所以受苦,仅仅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到她们。说起这件事,就令人害怕。可是玛丽埃塔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表示对此愤慨不已。
“您不用对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她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正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看到玛丽埃塔在向外甥卖弄风情,觉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她趁他们两人谈话间隙,插进去说,“明天晚上你上阿林家去,基泽维捷尔要在他家里布道,你也去吧,”她回过头去对玛丽埃塔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对他说了,他告诉我这是个好兆头。他说,你一定会回到基督的身边。你明天一定要去。玛丽埃塔,叫他一定要去。你自己也要去。”
“我,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要公爵做这做那,”玛丽埃塔望着涅赫柳多夫说,她用这种目光表示她和他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达到充分的默契。“其次,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你总是喜欢唱反调,自行其事。”
“我怎么是自行其是呢?我像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着说。“还有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见到过那个……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问。
玛丽埃塔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她演得棒极了。”
“那我先去看谁好呢,姨妈,先去看女演员还是先去看传教士?”涅赫柳多夫笑着说。
“请你别挑毛拣刺。”
“我以为还是先去看传教士,再去看法国女演员,要不,听他的说教就更加倒胃口了,”涅赫柳多夫说。
“不,还是先去看法国戏,再去忏悔,”玛丽埃塔说。
“行了,你们别拿我来取笑。传教士归传教士,看戏归看戏。为了拯救自己,完全不必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信了教,人就快活了。”
“姨妈,您比传教士还会传教。”
“这么办吧,”玛丽埃塔想了想说,“您明天到我包厢里来。”
“我担心会去不成……”
一个听差进来禀报说,有客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来客是慈善基金会的秘书,伯爵夫人就是这个团体的会长。
“这是个说起话来干巴巴的人,我还是换个地方接待他,等一会儿我再到这儿来。玛丽埃塔,你给他倒杯茶,”伯爵夫人说完,扭着腰肢,快步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埃塔脱下手套,露出一只扁平有力、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喝茶吗?”她说,古怪地翘起小指头,拿起搁在酒精灯上的银壶。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又忧郁。
“我很尊重别人的观点,他们却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我一想起这点,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似乎要哭出来了。虽然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思,即使有什么意思,也是含混不清的。但是涅赫柳多夫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异常真切,充满善意,这是因为这位年轻漂亮、衣着考究的女人说话时流露出来的炯炯放光的眼神将涅赫柳多夫迷住了。
涅赫柳多夫默默望着她,他的目光已经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了。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想些什么。其实您做的事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2),我钦佩您的作为,我赞成您。”
“说实话,我不值得别人钦佩,我做的事还很少。”
“这无关紧要。我了解您的感情,也了解她……好吧,好吧,我不再说这些了,”她发现涅赫柳多夫面有愠色,就收住话头。“不过我还了解,自从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惨状,”玛丽埃塔说,她一心想迷住他,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已经猜出他最看重和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他们由于别人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苦得无法忍受……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自己也愿意这样做,可是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难道您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吗?”
“我吗?”她问,心里感到十分惊讶,竟然有人会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我应该感到满意,因此也就满意了。可是我的心灵在觉醒……”
“不能再让它沉睡了,应该听听它的呼声,”涅赫柳多夫说,完全被她的谎言蒙骗了。
事后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地带着羞愧的心情回想起和她的谈话,回想起她那些与其说是谎言,倒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她说起监狱里种种惨状和自己对农村的印象时,她那副哀怜的表情。
伯爵夫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谈得不但像是两个老朋友,而且亲如知己,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似乎只有他们两个是心心相印的。
他们谈论当道者的不公正,不幸的人们的苦难,人民的贫困,但是在热烈的交谈中,他们没有忘记秋波传情,一个似乎在问:“你能爱我吗?”另一个回答:“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出人意料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她对涅赫柳多夫说,她愿意永远为他尽力效劳,还请他明天晚上务必到剧院去找她,哪怕去一分钟也好,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他。
“是啊,要不,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口气,补了一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着戒指的手上。“请您答应我一定来。”
涅赫柳多夫答应了。
这天晚上涅赫柳多夫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他躺到床上,吹灭蜡烛,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玛斯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仍旧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前来替他回答问题似的,他的眼前浮现出玛斯洛娃的脸,他看见她在叹息,她在说“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您”时的眼神和笑容,她的形象是那样清晰,好像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也笑了。“我将去西伯利亚,我这样做对吗?我放弃了财产,这样做对吗?”他问自己。
在这明亮的彼得堡的夜晚,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脑子里一团乱麻。他想召回以前的心情,重温以前的想法,然而,这些想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说服力。
“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万一我无法那样生活下去,万一我对我做的事后悔了,那该怎么办?”他问自己,但无法回答。他心里感到久未有过的惆怅和绝望,他无法理清这些问题,躺在床上,转辗反侧,好像打牌输了一大笔钱似的。
【注释】
(1)原文为法文。
(2)原文为法文。